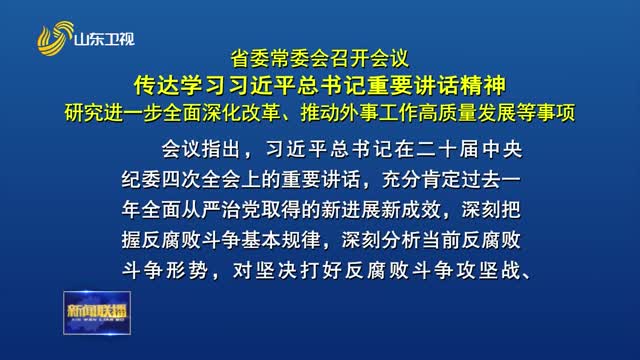那年,去相親
來源:檢察日報(bào)
2025-01-12 13:28:01
原標(biāo)題:那年,去相親
來源:檢察日報(bào)
原標(biāo)題:那年,去相親
來源:檢察日報(bào)
人人都有相親的經(jīng)歷。或電光火石、一見鐘情,或不曾來電、形同陌路。而我?guī)资昵暗囊淮蜗嘤H經(jīng)歷,雖說不上成敗,卻讓我銘心刻骨,難以忘懷。
那天,高中時(shí)的陳老師,讓我到某學(xué)校“看個(gè)人”。陳老師特意囑咐,“那個(gè)人”也是學(xué)中文的,對有寫作愛好的我“頗感冒”——就是有興趣的意思。本來一聽相親就別扭的我,忽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竊喜。
時(shí)間約在周日下午2點(diǎn)。按陳老師給的門號,輕輕敲門。隨著清脆的“請進(jìn)”聲,門隨之半開。
“你是?……你找誰?”一雙黑亮的大眼,忽閃著疑惑。
待我報(bào)上姓名,說明找誰,她把我讓進(jìn)屋,然后她先坐下。她椅子上,是碎布拼成圖案的坐墊。
“誰讓你來的?”她眼里的疑惑在翻騰。
我又報(bào)上介紹人姓名。我先前來時(shí)的溫?zé)嵝那椋鋈涣锪嘶荩б沧Р蛔 ?/p>
“坐吧。”她用腳推了下洗衣盆,擦擦手,指了指桌子對面的矮凳。坐上去,自然須仰視她。立時(shí),一種異樣的感覺涌滿胸腔。
此時(shí)才看清,這溢滿洗衣肥皂香味的房間,半拉著的素潔布簾,將書桌與床鋪隔開,顯然是辦公與臥室的混搭。
“找我有事嗎?”
“也沒……沒啥事。”她這不是明知故問嗎?這是審犯人嗎?我心里只罵自己,像吃了嗜好推糞球的什么郎!
進(jìn)門前,我還想象著:她是位笑意盈盈、善解人意的薛寶釵,抑或是柔聲細(xì)氣、詩意裊裊的林黛玉,盡管大我三兩歲,起碼洋溢著盧梭眼中華倫夫人般的魅力;同專業(yè)畢業(yè)的她,要么聊求學(xué)經(jīng)歷,要么聊中學(xué)生與師范生的差異,而我會(huì)條分縷析,娓娓闡述,以廣博的見識、聰穎的悟性,贏得她的信賴,進(jìn)而直抵她的芳心,至于能不能俘獲,那得靠造化了。
總之,絕不會(huì)跟以前相看的幾位,要么問我能否改行離開講臺,要么問我啥時(shí)候能調(diào)進(jìn)城。談教學(xué),聊文學(xué),那幾位不是打哈欠,就是顧左右而言他,簡直是對牛彈琴。
可眼前的這位,雙眸黑亮,不茍言笑,一尊冷顏,一副凜然的樣子。看來今日的相親懸乎了。如此想來,提著的心,倒安穩(wěn)落地了。
她在翻桌上的書,似乎找尋著什么,眼睛的余光,卻掃向桌前的我。
如此尷尬的場景,近乎凝滯的氣氛,不感到壓抑才怪。我深吸了一口氣,起身,推了推眼鏡,看墻上山口百惠與三浦友和的劇照。當(dāng)時(shí),他倆主演的電視連續(xù)劇《血疑》正風(fēng)靡一時(shí)。另一張是高倉健飾演的《追捕》中的杜秋。高倉健,三浦友和,一個(gè)硬漢,一個(gè)奶油小生,她的審美取向有些雜糅。
“你也喜歡日本電影?”剛才還在俯視我的她,終于輕啟芳唇。
“電影說不上喜歡,日本的作家倒喜歡幾位。”上大學(xué)時(shí),電影每周必看,這是文學(xué)作品欣賞課的需要。自從分配到山區(qū)中學(xué),三年了,我連電影幕布也沒再摸過。
“說說,喜歡川端康成的《雪國》,還是村上春樹的《且聽風(fēng)吟》?”她的眼中有了笑意,語氣漸趨溫婉和藹,似乎還透出些許愉悅。
“文學(xué)的生命是揭示人性。《雪國》像一首長長的浪漫散文詩,《且聽風(fēng)吟》更是青春劇。日本作家,我更欣賞魯迅的口味,偏愛被稱為東方卡夫卡的芥川龍之介,還有夏目漱石。”其實(shí),我特喜歡《雪國》《且聽風(fēng)吟》,川端康成、村上春樹的作品,讓上世紀(jì)80年代的大學(xué)生幾近瘋狂。可我不能入了她設(shè)的套,得另辟蹊徑,以展示我的與眾不同。
我掃了一眼,本以為她會(huì)不悅,卻見她剛剛還緊繃的面色和悅了,似乎在認(rèn)真傾聽著。我繼續(xù)說:“芥川的《羅生門》《鼻子》等,正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孔乙己》,是針砭社會(huì)時(shí)弊的‘匕首’‘投槍’。還有他的《秋山圖》《湖南的扇子》,寫起中國的畫家與國畫珍品,如數(shù)家珍,國人都難以企及。”
“揭示人性的作品,除了日本作家,西方文學(xué)里有哪些更具代表性?”她看我對日本作家不很陌生,顯然想岔開話題。
“西方的,揭示人性之惡的作家,莫過于法國的巴爾扎克,他的《人間喜劇》可謂扛鼎之作,還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英國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等戲劇;俄國托爾斯泰的《復(fù)活》,契訶夫的《套中人》《小公務(wù)員之死》……”
“你喜歡外國文學(xué),能記住幾部作品的開頭?”《安娜卡列尼娜》《懺悔錄》《羊脂球》《變形記》,我一連背了七八本小說的開頭,幾乎未假思索。
要說外國文學(xué),那可不是我的弱項(xiàng)。讀書時(shí),每逢周六周日,學(xué)院北側(cè)黨校的楊樹林里,兩個(gè)饅頭一杯水,背依樹干讀一天,捧著的幾乎都是外國名著。外國文學(xué)考試,最差的一次成績也88分,深得外國文學(xué)教授的賞識。
“《紅樓夢》的開頭背過嗎?”她忽然將我的思維拉回到中國古典文學(xué),讓我一愣,心里隨之一驚:人民出版社出的四冊《紅樓夢》,翻看過數(shù)遍,還真沒記住開頭。但不能示弱啊!我背了《三國演義》與《西游記》的開篇話。
“答非所問!”她嘴角微微一撇,卻讓我捕捉到了。“《紅樓夢》里,你最討厭哪幾個(gè)人物?舉例說說。”
“當(dāng)然是趙姨娘兒子賈瑞,跟老看門人焦大了。”我回答了,心里卻惴惴不安,一慌張,竟拿不準(zhǔn)趙姨娘兒子是賈瑞還是賈環(huán)?既然是“選擇題”,就蒙吧。當(dāng)年考沒學(xué)過的英語,全憑蒙呢!
“賈瑞父母早亡呢。趙姨娘的兒子不是環(huán)哥嗎?賈環(huán)盡管被其爺爺賈代儒嬌生慣養(yǎng),可下場凄慘,不該同情嗎?焦大盡管仰仗著危難時(shí)刻救過主子的命,說話有恃無恐,甚至做出出格的事兒,可都是生活在賈府最底層的人啊,不值得可憐嗎?!”她娓娓道來。
我突然感覺大腦短路,額頭似乎冒了汗。看我發(fā)窘,她微微笑了。靠前來,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坐下,像長者對待晚輩。她又去拿杯子倒水,似乎此刻才想起這應(yīng)有的禮節(jié)。
“古人說,半部《論語》治天下。要參透人生,解剖人性,一部《紅樓夢》就夠了,不是嗎?”看我抻后背汗?jié)竦囊r衫,她又微微一笑,“聽陳老師介紹,你教學(xué)之余堅(jiān)持寫作,發(fā)表了不少作品。也讓我拜讀學(xué)習(xí)下。”
遞過來的水杯,我放她桌上。我哪肯再坐。很想快快結(jié)束這“考試”,不,是“面試”。再耗下去,還不知會(huì)露出什么破綻來呢!“我該走了,還得趕回中學(xué)參加周前會(huì)。”
“記得給我看你的作品啊!”她站在門里,俯視著,分明是在叮囑臺階下的學(xué)生。
一扭身,走了。看什么看?除《中國青年報(bào)》《山東青年》刊載的《尊師路》《冬日,那一抹綠意》兩篇散文,《昌濰文藝》上一首蹩腳詩,其他都是通訊和消息。能拿得出手嗎?我心里自語道。
她的校園里,涼爽的秋風(fēng)吹拂,金黃的楊樹葉紛然飄落,也飄進(jìn)了我的內(nèi)心,紛亂雜蕪。膽怯了?羞愧了?后悔了?顯然都不是。后來想想,只是一種說不出、理不清的情緒如洇墨一樣,不受控地彌散而去。
(作者單位:山東省臨朐縣人民檢察院)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1800余萬元愛心資金物資支援抗震救災(zāi)
- 本報(bào)北京1月11日電“截至1月11日10時(shí),職基會(huì)已經(jīng)募集款物價(jià)值1800余萬元。”記者從中國職工發(fā)展基金會(huì)獲悉,西藏日喀則定日縣發(fā)生地震后,...[詳細(xì)]
- 工人日報(bào) 2025-01-12
讀懂更加積極財(cái)政政策的力度與溫度
- 讀懂更加積極財(cái)政政策的力度與溫度稿件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經(jīng)濟(jì)約10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項(xiàng)目清單提前下達(dá);江蘇、山東多地披露一季度地方債...[詳細(xì)]
- 新華每日電訊 2025-01-12
場景提檔升級 活力持續(xù)釋放
- 場景提檔升級活力持續(xù)釋放山東開年消費(fèi)市場掃描稿件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要聞新華社濟(jì)南1月11日電臨近春節(jié),位于山東省濟(jì)南市歷下區(qū)泉城路的蘇...[詳細(xì)]
- 新華每日電訊 2025-01-12
靈蛇獻(xiàn)瑞
- 這首樂曲由革命音樂家聶耳先生根據(jù)其故鄉(xiāng)昆明民樂改編而來,無論從音樂形象還是命名來看,都無不給人帶來力量與希望,充滿了畫面感。共工原...[詳細(xì)]
- 光明日報(bào) 2025-01-12
金石學(xué)史研究與刻帖書法新探
- 本報(bào)記者李亦奕以金石學(xué)史的方法感觸歷史金石學(xué),是“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fēng);上自經(jīng)史考...[詳細(xì)]
- 中國文化報(bào) 2025-01-12
以創(chuàng)作為核心探索畫院發(fā)展新路徑
- 云上220×220厘米2024年茹峰浙江畫院本報(bào)記者李百靈畫院是我國美術(shù)創(chuàng)作研究的重要力量,對于推動(dòng)新時(shí)代文藝繁榮發(fā)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日...[詳細(xì)]
- 中國文化報(bào) 2025-01-12

天道酬勤鑄不凡——《經(jīng)濟(jì)日報(bào)》聚焦青島港“人民工匠”許振超
- [詳細(xì)]
- 經(jīng)濟(jì)日報(bào) 2025-01-12

《新華每日電訊》頭版聚焦?山東開年消費(fèi)市場:場景提檔升級 活力持續(xù)釋放
- 山東省著力擴(kuò)大內(nèi)需,實(shí)施提振消費(fèi)十大專項(xiàng)行動(dòng),今年開年以來,消費(fèi)場景不斷提檔升級,消費(fèi)活力持續(xù)釋放。[詳細(xì)]
- 新華每日電訊 2025-01-12

尋魯味 過大年丨“好品山東·魯采年貨節(jié)”在京開幕
- 人民網(wǎng)北京1月11日電雖然天氣寒冷,卻阻擋不住市民熱情的腳步,紛紛到北京魯采三元橋“趕大集”,感受年味。1月10日,備受市民關(guān)注的“采物...[詳細(xì)]
- 人民網(wǎng)山東頻道 2025-01-11
全國公安機(jī)關(guān)開展系列活動(dòng)
- 本報(bào)北京1月10日電1月10日是第五個(gè)中國人民警察節(jié)。記者從公安部獲悉 10日,全國公安機(jī)關(guān)和廣大公安民警開展了升警旗、唱警歌、重溫入警誓...[詳細(xì)]
- 人民日報(bào) 2025-01-11
老面饅頭“蒸”出鄉(xiāng)村新氣象
- 在山東省青島市西海岸新區(qū)海青鎮(zhèn)甜河村共富茶食聯(lián)營工坊內(nèi),工作人員正在熱火朝天地制作傳統(tǒng)老面饅頭。該工坊通過批量化、標(biāo)準(zhǔn)化生產(chǎn)饅頭、...[詳細(xì)]
- 農(nóng)民日報(bào) 2025-01-11
從“就近就便”轉(zhuǎn)向“就優(yōu)就好”
- 近日,山東濰坊坊子區(qū)黃旗堡街道中心小學(xué)學(xué)生家長王成山告訴記者,他的孩子原本在黃旗堡街道逄王小學(xué)就讀。曾經(jīng)的逄王小學(xué),全校僅有19名平...[詳細(xì)]
- 中國教育報(bào) 2025-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