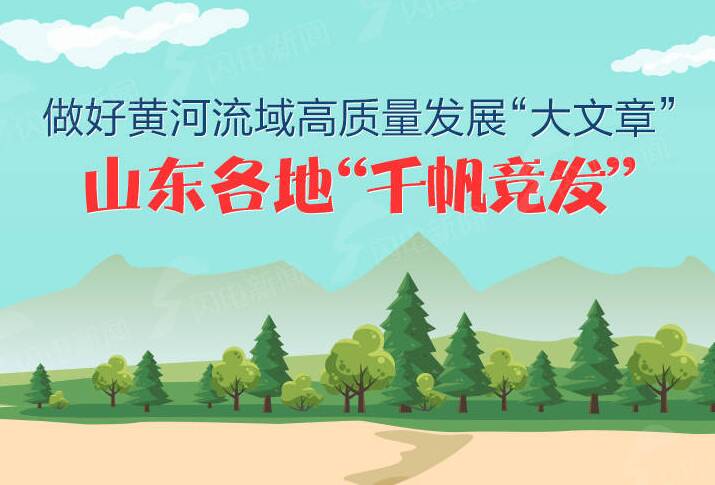用迷霧般語言向納博科夫致敬 深圳女孩首部長篇一鳴驚人
來源:華西都市報
2020-09-27 15:57:09
用迷霧般語言向納博科夫致敬 深圳女孩首部長篇一鳴驚人
9月15日,備受年輕讀者關注的2020年第三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決選名單公布。經(jīng)過評委會成員蘇童、孫甘露、西川、楊照、張亞東按照多數(shù)原則表決,進入決選名單的五部作品如下:林棹《流溪》、任曉雯《浮生二十一章》、沈大成《小行星掉在下午》、雙雪濤《獵人》、徐則臣《北京西郊故事集》。
徐則臣是國內中青年文學實力中堅派代表,2019年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雙雪濤是近些年崛起的80后作家。任曉雯和沈大成都是近幾年作品頻出的70后實力作家。相比而言,林棹這個名字在文壇顯得比較陌生。
林棹是誰?《流溪》寫了什么?有怎樣的特色?為什么能一鳴驚人?自然也引發(fā)一些讀者的好奇。
《流溪》是林棹創(chuàng)作并發(fā)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首發(fā)于《收獲》雜志2019夏季長篇專號,2020年4月小說由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如果按照閱讀小的常規(guī)方法,試圖厘清她到底講了什么故事,那么大概可以這么總結:小說以女主人公張棗兒的敘述展開,回望了童年、少年生活,以暴虐的父親和絕望的母親為代表的家族群像,和與浪蕩情人楊白馬的失意戀情。
作為一部字數(shù)十萬出頭的作品,《流溪》最大特點是,文本的節(jié)奏、質感,很獨特。納博科夫式的傾訴和描述,帶來了強烈的陌生感和挑戰(zhàn)感。迷霧般的語言,寶石般的幻象與狂想,引領我們仿佛走進一個歷史和當下,回憶與當下,夢幻與現(xiàn)實交織的思想?yún)擦帧_@部處女作充滿難以描摹的幻象、狂想,天馬行空的修辭,豐富的細節(jié),多義的詞匯與符號,將讀者帶進前所未有的意識漩渦,每一次重讀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和發(fā)現(xiàn)。
這部作品也受到詩人翟永明和作家棉棉的好評推薦。
林棹1984年5月出生在廣東深圳。2005年,當時21歲的她就完成了《流溪》初稿,但稿件一度丟失。2018年找到后,林棹改寫,完稿。跟很多有寫作理想但容易被現(xiàn)實生活帶離她從事文學的年輕人軌跡相似,不寫作的林棹也從事過跟寫作完全無關的工作,比如實境游戲設計,賣過花,種過樹。
2018年一場大病讓她決心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重拾文學寫作,最終完成了《流溪》。
2020年9月,在2020年第三屆理想國文學獎決選名單公布后,封面新聞記者聯(lián)系到林棹,對她進行了專訪。
“《流溪》是21歲的我和34歲的我合力完成的”
封面新聞:《流溪》是你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入選了“2020年第三屆理想國文學獎決選名單”,感覺怎么樣?
林棹:高興。
封面新聞:《流溪》跟我讀過的很多小說不都一樣:它沒有常規(guī)的敘事,形式上很先鋒。你是受到哪位作家的啟發(fā)或者影響比較大?
林棹:知道納博科夫是在2003年前后,文學論壇里,他和好幾位作家一起,被小范圍地喜愛、分享。他的長篇文本,因為密度大、細節(jié)精美,往往在三讀之后才徹底綻放。字里行間,你眼見他玩得精妙、投入、高興。那是一種極具感染力和魅力的示范:如果文字是小說的唯一材料,它可以發(fā)展到一個什么程度,它可以為作者和讀者帶去什么程度的欣喜;當然它同時帶來一些問題——對納博科夫主義者來說則不是問題——諸如,審美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嗎?
在納博科夫之前我讀過許多村上春樹的書。村上春樹就像某種青春期大門,納博科夫則是一座轟然降落的寶石山,太異質了,以至于,對形式上的“驚奇”和“陌生感”的追求從此變成一種閱讀上的偏執(zhí)。這種偏執(zhí)可能讓我錯失了一些東西。
封面新聞:能談談這部小說嗎?作為寫作者你寄托給這部小說的是要表達什么?而完成它又經(jīng)歷過怎樣的過程?
林棹:《流溪》的前后兩稿,是21歲的我和34歲的我合力完成的。當中的十三年,它以未能確定的形式躺在未能確定之處。現(xiàn)在可以把它當做一個比喻了,因為它被寫完、擁有了確定的結局。它可以是關于成長的比喻,關于時間的比喻,關于際遇的比喻,諸如此類。而在被寫完之前,它只是一個洞,被記著或被忘記。
21歲的我缺乏認知、經(jīng)驗、勇氣,但不要緊,因為每個人在每個年齡段總會缺點兒什么;34歲的我擁有了這些,外加一點運氣,于是很幸運地,可以動手把那個洞填起來。對我來說,洞變成了橋。有時,寫作者和作品之間是互相救濟的關系。
至于“小說要表達什么”,我倒覺得不必急于概括——小說恰好是反概括的,它是細節(jié)、細節(jié)和細節(jié),具體、具體和具體。它是親歷。
“我記得成都冬春季的清晨時常起霧”
封面新聞:這部作品里,應該有一些真實的生活或者人物影子。其中真實和虛構,是怎樣的關系?
林棹:現(xiàn)實世界的非虛構性日漸松動,虛構世界則勉力虛構真實,兩者共通的迷人之處在于,“真實”以神秘、不可測算的尺度扭轉、變形,這一“不可測算”對作者和讀者而言都成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每個角色都是我。“我”、爸爸媽媽、那排玉蘭樹、牛奶、失去牛奶的牛奶杯,都是我。于是我打我,我親吻我,我沖著我喋喋不休……而小說中提及的城市,比如成都,變形作“濃霧城”——我記得成都冬春季的清晨時常起霧,伴隨一種濕的低溫,建筑物頭頸胸消失,世界軟化成乳白的流體——惟有主觀的真實留存。
封面新聞:我看到報道說,“2005年她完成了這部小說的初稿,稿件一度丟失。2018年被找到后,林棹改寫,完稿……”成稿過程中遇到哪些困難,是如何克服的?
林棹:20歲的時候,我對世界、對生活一無所知,但生活早就開始了,那個生活是先于你存在的、等待你去延續(xù)或打破的盒子。在我的盒子里,人們會認為想要寫小說為生是瘋了,畢業(yè)、拿工資、退休的路徑才是正常、可靠。我一度接受了這個理念,因為我二十幾歲,對世界和生活一無所知,性格謹慎保守。類似于,寫作是一份禮物,我極端渴慕,卻相信自己絕不可能得到,于是不僅放棄了,還躲得遠遠的。重新寫作之前一直是這個心態(tài)。
封面新聞:后來是怎么又重拾文學寫作的?
林棹:2017年底,無端地開始做一點小練筆。覺得特別帶勁。2018年初旅行時撞上流感,病毒性心肌炎,幾乎死掉,但是活了過來。我覺得那就是運氣:重病和病愈,來得又快又急,一場極度逼真的死亡模擬。經(jīng)歷過的人,恐怕都會重新打量生活,掂量清楚什么才是真正快樂和值得過的人生。那年我34歲,那場病幫我做了全職寫小說的決定——一方面身體需要靜養(yǎng)康復;另一方面家屬全力支持。
封面新聞:作品起名“流溪”,是怎么想的?
林棹:相比自上而下的、大的、外向或關注群體的探索,《流溪》是關注個體的、內向的、近距離的,溪水的意象符合這些特征。個體的聲音深埋在群山密林之中,需要凝神傾聽,同時那些傾訴也如溪水一樣萬變、充滿不確定性。
封面新聞:可否介紹一下你的下一部作品?
林棹:第二部長篇已經(jīng)完稿,從19世紀初的廣州出發(fā),循著江河、海洋擴展,文字上做了方言寫作的試探。對我來說它是很有意義的一段旅程,把我送至充滿驚奇和陌生感的天地,其中的一切靜待喚醒……
封面新聞記者張杰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打出“組合拳” 引來鳳凰棲——天津濱海新區(qū)外企發(fā)展一線見聞
- 新華社天津9月27日電。題 打出“組合拳”引來鳳凰棲——天津濱海新區(qū)外企發(fā)展一線見聞。走進位于天津濱海新區(qū)的古德里奇航空結構服務(中國...[詳細]
- 新華網(wǎng) 2020-09-27
警惕“無糖月餅”致血糖、血壓升高
- 新華社長沙9月27日電(記者帥才)中秋節(jié)臨近,湖南省中醫(yī)藥研究院附屬醫(yī)院老年病科主任袁春云教授提醒,月餅雖然美味,但患有糖尿病、心腦...[詳細]
- 新華網(wǎng) 2020-09-27
河南無臂小伙直播賣花生:10天完成首單,掙5角錢
- 26歲的孫亞輝是一名無臂青年,他在淘寶平臺上開有一家店鋪,名字就叫“做個有用的人兒”。家里2畝田產(chǎn)的一千多斤花生,成了小店上架的第一...[詳細]
- 大河網(wǎng) 2020-09-27

文化和旅游部:旅游和文化市場復工復產(chǎn)有序推進 中秋國慶八天長假旅游人數(shù)預計達5.5億人次
- [詳細]
- 齊魯網(wǎng) 2020-09-27
半月談 | 月餅“早產(chǎn)”? 食品標簽里,多少糟心事
- 食品標簽里,多少糟心事。雖然各地市場監(jiān)管部門每年都會進行食品標簽標識領域的日常監(jiān)管和專項檢查,但食品標簽標識違法亂象仍時有發(fā)生,各...[詳細]
- 新華社 2020-09-27
“大道康莊”河北篇:回到阜平的年輕人
- 【人物特稿】回到阜平的年輕人。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陸續(xù)歸來,奮斗圓夢,為家鄉(xiāng)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劉云清 “帶著村民一起致...[詳細]
- 人民網(wǎng) 2020-09-27
雙節(jié)假期期間北京劇院、景區(qū)限流由50%上調至75%
- 在27日北京市文旅局召開的“迎雙節(jié)、促發(fā)展”系列文旅活動新聞通氣會上,北京市文旅局副局長曹鵬程表示,文化和旅游部日前發(fā)布的《劇院等演...[詳細]
- 新華社“新華視點”微博 2020-09-27
蘭州新區(qū)“無圍墻”職教園:共享共用打造絲路“工匠搖籃”
- 圖為建設中的蘭州新區(qū)職教園區(qū)。”蘭州新區(qū)職教園區(qū)教學實訓管理科科長魏物春說,共享實訓中心,在引進先進硬件的同時,也吸納了像西門子、...[詳細]
- 中國新聞網(wǎng) 2020-09-27
中國農(nóng)科院創(chuàng)制出玉米密植高產(chǎn)綠色生產(chǎn)新技術體系
- 新華社北京9月27日電中國農(nóng)業(yè)科學院的一個科研團隊經(jīng)過多年研究,創(chuàng)制出玉米密植高產(chǎn)潛力挖掘、機械粒收與全程機械化生產(chǎn)、水肥一體化資源...[詳細]
- 新華網(wǎng) 2020-09-27
為節(jié)約7毛錢“走斷腿” 如今一半村民有了小汽車
- 重慶市南川區(qū)山王坪鎮(zhèn)廟壩村的脫貧之路為節(jié)約7毛錢“走斷腿”如今一半村民有了小汽車。如今,廟壩村以種植黃連、筍竹,養(yǎng)殖中蜂和鄉(xiāng)村旅游...[詳細]
- 華西都市報 2020-09-27
華為斷供十日:員工保持狼性 “絕版”產(chǎn)品被熱炒
- “華為終端已經(jīng)走到了最困難的時刻。”兩周前,華為消費者業(yè)務CEO余承東在開發(fā)者大會上,向外界透露了華為即將面臨的困境——5天后,美國的...[詳細]
- 東方網(wǎng) 2020-09-27
央行持續(xù)投放短期流動性 隔夜Shibor跌破1%
- 新華社北京9月27日電題 央行持續(xù)投放短期流動性隔夜Shibor跌破1%。中國人民銀行27日開展了200億元14天期逆回購操作。在近期央行持續(xù)投放短...[詳細]
- 新華網(wǎng) 2020-09-27
北京無喙蘭 首現(xiàn)霧靈山
- 北京無喙蘭首現(xiàn)霧靈山。本報訊日前,霧靈山自然保護區(qū)傳來喜訊,科考人員在此地發(fā)現(xiàn)了唯一以北京命名的蘭科植物——“北京無喙蘭”和京津冀...[詳細]
- 北京晚報 2020-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