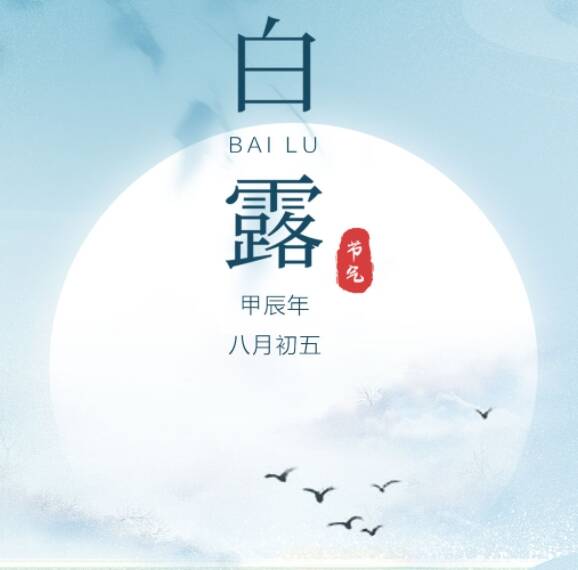“寅賓出日” 的煙臺(tái)考證
來(lái)源:煙臺(tái)日?qǐng)?bào)
2024-09-10 18:24:09
原標(biāo)題:“寅賓出日” 的煙臺(tái)考證
來(lái)源:煙臺(tái)日?qǐng)?bào)
原標(biāo)題:“寅賓出日” 的煙臺(tái)考證
來(lái)源:煙臺(tái)日?qǐng)?bào)
吳忠波
煙臺(tái)是人類(lèi)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區(qū)之一,在這里居住的人自古以來(lái)就崇拜太陽(yáng)。在芝罘區(qū)西南部的白石村,距今海岸約1.5千米處,7000多年前有一個(gè)小型港灣。白石人在這里以海捕和農(nóng)耕為謀生手段,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史前文化。
長(zhǎng)島也是東夷民族的家園之一。距今6500年到4000年的北莊遺址,位于大黑山島北莊村,因形態(tài)與西安半坡遺址相似,被專(zhuān)家稱(chēng)為“東半坡”。在這里出土的一塊陶片上,刻有數(shù)個(gè)太陽(yáng)紋;還有的陶器上刻有鳥(niǎo)類(lèi)形象,這說(shuō)明東夷人是非常崇拜太陽(yáng)的。另外,長(zhǎng)島南部群島的地形分布,古往今來(lái)都有“左龍(南北長(zhǎng)山)、右虎(大小黑山)、丹鳳(廟島)、朝陽(yáng)(太陽(yáng)島)”的傳說(shuō)。這自然為古今長(zhǎng)島打上了太陽(yáng)崇拜的標(biāo)簽。
看日出,煙臺(tái)人已司空見(jiàn)慣。而今年5月4日華晨宇在演唱會(huì)上“唱出太陽(yáng)”,為煙臺(tái)這座“山海名邦”(蘇軾語(yǔ))注入了青春活力。“向陽(yáng)而生”已成為城市文旅的新亮點(diǎn),也鉤沉了古代“寅賓出日”(意為恭敬地迎接即將升起的太陽(yáng))的輝煌歷史。
寅賓出日是古代中國(guó)的禮儀,表達(dá)了人們對(duì)太陽(yáng)的崇拜之情和對(duì)農(nóng)業(yè)豐收的祝福之意。與寅賓出日有關(guān)的傳說(shuō),大都出現(xiàn)在古代的渤海、北海、東海,即今天的渤海、黃海一帶。
記載諸多神話(huà)的《山海經(jīng)》,很可能是活躍于山東半島一帶的大汶口文化或膠東半島的原始知識(shí)遺存。2009年10月18日,筆者采訪(fǎng)北京大學(xué)的終身教授嚴(yán)文明先生時(shí),他說(shuō):“神話(huà)傳說(shuō)發(fā)生(源)地,要有人類(lèi)的環(huán)境、氛圍和歷史作背景,長(zhǎng)島(煙臺(tái))是古代人類(lèi)文明的(一個(gè)重要)發(fā)祥地,所以擁有眾多神話(huà)傳說(shuō)傳至今日。”
神話(huà)傳說(shuō)、史前遺址、上古巖畫(huà)、“八主”陳?ài)E、詩(shī)詞傳世、賓日建筑等,都為寅賓出日的絢麗底色,涂抹上了一筆濃墨重彩。
神話(huà)傳說(shuō)中的太陽(yáng)崇拜
日出扶桑。關(guān)于《山海經(jīng)》的扶桑神話(huà)發(fā)源地有兩種說(shuō)法,其中一種說(shuō)法是,扶桑是遠(yuǎn)古時(shí)期東海里的一棵神樹(shù),太陽(yáng)從那里升起。
登州是古代東海沿岸最古老的文明聚落之一。“日出扶桑”于登州,讓歷代文學(xué)家筆下生花。唐代獨(dú)孤及在《觀海》詩(shī)中說(shuō):“白日自中吐,扶桑如可捫。”宋代蘇軾在《望海》中提到:“黃昏風(fēng)絮定,半夜扶桑開(kāi)。”明代王世貞在《蓬萊閣后》中寫(xiě)道:“高城鐘鼓喚蒼茫,海若镕波浴太陽(yáng)。綺色中天徐散盡,空青一點(diǎn)是扶桑。”顧應(yīng)祥在《游珠璣巖》中說(shuō):“芒鞋飛下珠璣巖,遙望扶桑指顧間。”清代施閏章在《望日樓觀日出》中寫(xiě)道:“車(chē)輪燁燁從中躍,赤烏飛起彩云落。光芒倒射黿鼉宮,扶桑枝罥蓬萊閣。”任璇在《登蓬萊閣》中寫(xiě)道:“扶桑知不遠(yuǎn),好待日華曛。”崔應(yīng)階在《登蓬萊閣二首》中寫(xiě)道:“日出扶桑霞煥彩,月明珠島蚌生胎。”
這些詩(shī)中所寫(xiě)的扶桑,都為東海日出處。“日出扶桑”,被列為清代蓬萊十大景之一。徐人鳳解讀說(shuō):“海云沆漭覆虞淵,駿烏宵騰羲馭還。何必燭龍銜始出,滄波原是接長(zhǎng)天。”
羲和浴日。羲和浴日也是《山海經(jīng)》中記載的上古神話(huà)。據(jù)《山海經(jīng)·大荒南經(jīng)》記載:“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guó)。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太陽(yáng)女神羲和生的十個(gè)太陽(yáng),住在東方海外湯谷,有一樹(shù)和一地,都叫“扶桑”。太陽(yáng)們住在幾千丈高的大樹(shù)上,每天輪流在天空值班。值班時(shí),由羲和駕著龍車(chē)相送。
從起點(diǎn)湯谷到終點(diǎn)蒙谷,一天的路程共有十六個(gè)站。龍車(chē)到達(dá)第十四站悲泉,值班太陽(yáng)便下車(chē)步行,羲和駕空車(chē)趕回湯谷為明天作準(zhǔn)備。值班太陽(yáng)登上龍車(chē)之前,先在咸池里沐浴。
遠(yuǎn)古的太陽(yáng)神話(huà),造就了羲和的原始形態(tài),時(shí)代更迭又使她由最初的“日母”演變成了“日御”,由部落演變成了歷官,承擔(dān)了文化的載體功能,賦能于古詩(shī)詞的文化環(huán)境。
射逐太陽(yáng)。山東作為古老的東夷族群居住地(東夷系指中原之東方人,是中國(guó)古代尤其是商朝、周朝時(shí)期,對(duì)中國(guó)東部海濱不同部族的泛稱(chēng)),歷來(lái)流傳著與太陽(yáng)有關(guān)的傳說(shuō),其中便有人們熟知的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
《楚辭章句》中記載:“堯時(shí)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上世紀(jì)九十年代,長(zhǎng)島月牙灣景區(qū)曾有后羿射日的石雕。
《山海經(jīng)·海外北經(jīng)》記載:“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煙臺(tái)先民的“太陽(yáng)崇拜”
從這些神話(huà)故事中,我們能夠感受到古人對(duì)太陽(yáng)的信仰,也能反映出中華文明的“太陽(yáng)崇拜”源遠(yuǎn)流長(zhǎng)。除了傳說(shuō),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一些文物,也佐證了古人的日神信仰。
1960年,山東莒縣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刻有日月崇拜圖像,后來(lái)山東諸城前寨上也出土過(guò)一件,圖案相同,還涂有朱紅顏色。圖像下邊像座山,中間是彎月,上邊是太陽(yáng),將日、月、山全部表現(xiàn)了出來(lái)。
這些圖像,古人刻于距今五千多年前,可能與祭天、祈年等活動(dòng)有關(guān)。這是中國(guó)目前發(fā)現(xiàn)的最原始的天文圖案,都蘊(yùn)涵著關(guān)于太陽(yáng)的傳說(shuō)。大汶口中晚期的陶鬹(鬹gui,炊煮器)及龍山文化的鳥(niǎo)喙足鼎,也是太陽(yáng)崇拜與鳥(niǎo)信仰相結(jié)合的生動(dòng)例證。
煙臺(tái)是人類(lèi)最早繁衍生息的地區(qū)之一,在這里居住的人自古以來(lái)就崇拜太陽(yáng)。在芝罘區(qū)西南部的白石村,距今海岸約1.5千米處,7000多年前有一個(gè)小型港灣。白石人在這里以海捕和農(nóng)耕為謀生手段,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史前文化。
長(zhǎng)島也是東夷民族的家園之一。距今6500年到4000年的北莊遺址,位于大黑山島北莊村,因形態(tài)與西安半坡遺址相似,被專(zhuān)家稱(chēng)為“東半坡”。在這里出土的一塊陶片上,刻有數(shù)個(gè)太陽(yáng)紋;還有的陶器上刻有鳥(niǎo)類(lèi)形象,這說(shuō)明東夷人是非常崇拜太陽(yáng)的。
另外,長(zhǎng)島南部群島的地形分布,古往今來(lái)都有“左龍(南北長(zhǎng)山)、右虎(大小黑山)、丹鳳(廟島)、朝陽(yáng)(太陽(yáng)島)”的傳說(shuō)。這自然為古今長(zhǎng)島打上了太陽(yáng)崇拜的標(biāo)簽。
日出巖畫(huà)的煙臺(tái)發(fā)現(xiàn)
人類(lèi)的祭日活動(dòng),是崇拜太陽(yáng)的實(shí)際行動(dòng),古代巖畫(huà)則記錄了人們的日月祭祀習(xí)俗。中國(guó)已發(fā)現(xiàn)非常豐富的日月崇拜巖畫(huà),其中有不少拜日、祭天、祈求豐年的活動(dòng)場(chǎng)面。
在江蘇連云港將軍崖發(fā)現(xiàn)的巖石刻畫(huà)中,刻畫(huà)著一幅祭天的場(chǎng)面,有太陽(yáng)、星象、禾苗、人像等造型。這是我國(guó)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幅反映東夷部落生活的歷史畫(huà)卷,距今已有一萬(wàn)年的歷史。
據(jù)煙臺(tái)文史學(xué)者林治永研究,膠東半島地區(qū)與所在海岱地區(qū)也有龍山文化時(shí)期的巖畫(huà)分布,可與中原地區(qū)和西北地區(qū)的巖畫(huà)相媲美。經(jīng)過(guò)近十年的業(yè)余田野考察,林治永已發(fā)現(xiàn)成片和零散巖畫(huà)三百余處,其中與太陽(yáng)和天象相關(guān)的有幾十處。
已發(fā)現(xiàn)的巖畫(huà)遺跡,多分布在齊地八主神祠附近。煙威地區(qū)分布在榮成、萊州、牟平、蓬萊、福山、招遠(yuǎn)、棲霞、長(zhǎng)島等地。其特點(diǎn)是,靠海的地方,發(fā)現(xiàn)的數(shù)量較多;而州府所在地、居住密度大、建筑設(shè)施多的區(qū)域,數(shù)量相對(duì)較少。這些太陽(yáng)巖畫(huà)的圖像有三陽(yáng)縱排列、三日呈三角和立竿見(jiàn)影形等。
林治永對(duì)不可移動(dòng)巖畫(huà)的發(fā)現(xiàn),對(duì)其中六十件可移動(dòng)巖畫(huà)的收藏,實(shí)現(xiàn)了半島巖畫(huà)研究和收藏零的突破,也證實(shí)了考古泰斗蘇秉琦先生在上世紀(jì)九十年代斷言的半島地區(qū)肯定有巖畫(huà)的判斷。這也反映出,煙臺(tái)是中華文明沐浴第一縷陽(yáng)光的地方之一。
齊地的八主崇拜和祭祀,自古就有,或是由姜太公創(chuàng)造,并建立起信仰體系。這“八主”除天主淄博、地主和兵主泰安外,其他五主均在青、煙、威:陰主,神祠在三山(今煙臺(tái)萊州);陽(yáng)主,神祠在之罘(今煙臺(tái)芝罘);月主,神祠在萊山(今煙臺(tái)龍口);日主,神祠在成山(今威海成山);四時(shí)主,神祠在瑯邪(今青島瑯琊)。可見(jiàn)膠東半島的日月星辰,是當(dāng)時(shí)民間崇拜的偶像,也是帝王自然崇拜的理想之所。
陰主祠在三山島附近的過(guò)西村,據(jù)考是夏代方國(guó)所在地。陽(yáng)主祠之罘在先秦時(shí)期是著名的港口轉(zhuǎn)附。日主祠成山在臨海最東端,是最早迎接海上日出的地方。月主祠萊山北是西周時(shí)期萊國(guó)都城歸城的所在地。秦皇漢武曾先后多次登臨這些地方。《漢書(shū)·地理志》記載,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途經(jīng)黃縣(月主),攀成山(日主),登之罘山(陽(yáng)主),再登瑯邪山(四時(shí)主)。《漢書(shū)·武帝紀(jì)》記載,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二月,漢武帝“幸瑯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
北宋蘇軾任知登州時(shí),感懷并敬畏這些日月祭祀遺跡,形容“俗近齊魯之厚,跡皆秦漢之陳”(《登州謝兩府啟》)。他看慣了江河日出,卻更著迷于觀賞登州的海上日出。于是,他在上呈的《登州謝兩府啟》中,書(shū)寫(xiě)了“賓出日于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于海嶠,鼓角清閑”的話(huà)語(yǔ),表達(dá)了他的觀感和心跡。
登州蓬萊曾建有日賓樓(后來(lái)又叫望日樓)。日賓樓八角雙層十六柱,木質(zhì)結(jié)構(gòu),乃觀日佳處。蘇軾的《書(shū)自作木石》中便有“與同僚飲酒日賓樓上”的詩(shī)句。
此樓觀海望日,壯麗磅礴,也受到后代文人的青睞。清代詩(shī)人、官員施閏章就曾寫(xiě)過(guò)《望日樓觀日出》一文:“日初出時(shí),一線(xiàn)橫袤,如有方幅棱角,色深赤,如丹砂。已而,焰如火,外有絳帷浮動(dòng),不可方物。久之,赤輪涌出,厥象乃圓,光彩散越。不彈指而離海數(shù)尺,其大如鏡,其色如月矣。”
“寅賓出日”在棲霞岠嵎山
棲霞,是煙臺(tái)唯一不靠海的縣級(jí)市,曾為“祭日于壇”之地。據(jù)此,棲霞岠嵎山一帶,有可能是嵎夷文化的發(fā)祥地所在。
建炎四年(1130年),劉豫建立齊國(guó),被持正統(tǒng)史觀者稱(chēng)為偽齊,存世八年。金天會(huì)九年(1131年),劉豫在膠東地區(qū)同時(shí)設(shè)置了招遠(yuǎn)、福山、棲霞三個(gè)縣。棲霞方山,朝陽(yáng)初升,霞光萬(wàn)道;落日西墜,云蒸霧繞,是膠東半島的地理中心。山上存有大量的祭壇、大路、石墻,經(jīng)過(guò)實(shí)測(cè),具有天文觀測(cè)和祭祀天地日月的功能。劉豫深知,這是一處遠(yuǎn)古祈福的圣地。于是,為烘托祥瑞,他認(rèn)定方山是霞光和太陽(yáng)棲息的地方,為《山海經(jīng)》中記載的羲日所在,以及《尚書(shū)·堯典》中羲仲寅賓出日、測(cè)定春分的嵎夷、旸谷所在。
棲霞為旸谷所在地的說(shuō)法在當(dāng)?shù)卮鱾鳌C骷尉溉吣辏?558年),棲霞知縣李揆在縣署內(nèi)儀門(mén)東側(cè)修建“寅賓館”,紀(jì)念“寅賓出日”這一經(jīng)典事跡。明萬(wàn)歷六年(1578年)鮑霖任知縣期間,棲霞城垣經(jīng)修繕形成規(guī)模,增設(shè)寅賓(迎日)、環(huán)翠(抱山)、迎恩(拜廷)、迎仙(遙海)“四門(mén)”。東門(mén)取名“寅賓”,呼應(yīng)羲仲在嵎夷旸谷“寅賓出日”的典故。
日出東方帶來(lái)的啟示
無(wú)論是神話(huà)傳說(shuō),還是考古發(fā)現(xiàn),都向我們印證了膠東半島與“日出東方”的淵源。煙臺(tái)在山東和膠東半島的東端,是東方太陽(yáng)升起較早的地方,不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舊時(shí)代生產(chǎn)方式,還是“朝沐黃海,落霞渤海”的新時(shí)代生活追求,都有著崇日指向和朝陽(yáng)象征。
上世紀(jì)六十年代,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了大型舞蹈史詩(shī)《東方紅》,開(kāi)頭的日出畫(huà)面,便是取景于蓬萊的日賓樓。上世紀(jì)末,吳祖光所寫(xiě)的《長(zhǎng)島看日出》、劉白羽所寫(xiě)的《煙臺(tái)山看日出》,分別列入中國(guó)100篇散文精粹和煙臺(tái)2019讀書(shū)日必讀文章。新世紀(jì),煙臺(tái)圍繞日出開(kāi)發(fā)了許多旅游景區(qū)景點(diǎn),也打造了打卡地和旅游場(chǎng)景。直到今年華晨宇演唱會(huì)的日出場(chǎng),以“向陽(yáng)而生”的演唱重啟了煙臺(tái)日出的按鍵,打出了“日出東方”的古老標(biāo)簽。各級(jí)政府的支持、文旅相關(guān)部門(mén)的協(xié)作,使這一優(yōu)勢(shì)資源得以重新挖掘,迎來(lái)了近年來(lái)少有的“潑天流量”。
煙臺(tái)的“寅賓出日”,歷史底色鮮亮,現(xiàn)實(shí)傳承迫切。我們也期待通過(guò)“寅賓出日”、向陽(yáng)而生的探索,為仙境海岸、品重?zé)熍_(tái)研究開(kāi)啟一條路徑,增添一抹亮色。
想爆料?請(qǐng)登錄《陽(yáng)光連線(xiàn)》(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xiàn)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xiàn)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xiàn)0531-81695052,誠(chéng)邀合作伙伴。
全球木材與木制品大會(huì)在日照召開(kāi)
- □記者吳寶書(shū)丁兆霞報(bào)道本報(bào)日照9月5日訊今天,為期三天的2024全球木材與木制品大會(huì)暨中國(guó)木結(jié)構(gòu)和旅居產(chǎn)業(yè)展覽會(huì)在日照開(kāi)幕,來(lái)自全球的近...[詳細(xì)]
- 大眾日?qǐng)?bào) 2024-09-10
煙臺(tái)車(chē)務(wù)段暑運(yùn)發(fā)送旅客700余萬(wàn)人次
- □記者楊秀萍通訊員王丹報(bào)道本報(bào)煙臺(tái)訊記者從煙臺(tái)車(chē)務(wù)段獲悉,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為期62天的鐵路暑運(yùn)圓滿(mǎn)收官,煙臺(tái)車(chē)務(wù)段共計(jì)發(fā)送旅客7...[詳細(xì)]
- 大眾日?qǐng)?bào) 2024-09-10
走,沿著煙臺(tái)首條“慈善線(xiàn)路”去打卡
- 本報(bào)訊今年9月5日是第九個(gè)“中華慈善日”,圍繞“崇德向善依法興善”主題,我市舉行第九個(gè)“中華慈善日”集中宣傳月暨公益慈善嘉年華啟動(dòng)儀...[詳細(xì)]
- 煙臺(tái)晚報(bào) 2024-09-10
山東嶧城石榴文化創(chuàng)意設(shè)計(jì)大賽啟動(dòng)
- □孟令洋報(bào)道本報(bào)棗莊訊為助推石榴產(chǎn)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和鄉(xiāng)村振興,棗莊市近日舉辦2024山東嶧城石榴文化創(chuàng)意設(shè)計(jì)大賽。本屆大賽分為主題賽和青年...[詳細(xì)]
- 大眾日?qǐng)?bào) 2024-09-10
山東老年大學(xué)調(diào)研組 來(lái)我區(qū)調(diào)研
- 東昌府訊9月3日,山東老年大學(xué)綜合規(guī)劃處處長(zhǎng)柴利華一行,來(lái)我區(qū)調(diào)研了解《關(guān)于推進(jìn)新時(shí)代全省老年大學(xué)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意見(jiàn)》貫徹落實(shí)情況。調(diào)...[詳細(xì)]
- 東昌時(shí)訊 2024-09-10
金融為民譜新篇 守護(hù)權(quán)益防風(fēng)險(xiǎn)丨太平人壽煙臺(tái)中支2024年金融教育宣傳月之消費(fèi)提示
- 為扎實(shí)推進(jìn)金融教育宣傳工作,提升全市廣大消費(fèi)者的金融知識(shí)素養(yǎng),2024年金融教育宣傳月,太平人壽煙臺(tái)中心支公司特開(kāi)展金融教育知識(shí)普及工...[詳細(xì)]
- 水母網(wǎng) 2024-09-10
泰安兩項(xiàng)目入選省級(jí)試點(diǎn)名單
- □記者劉濤報(bào)道本報(bào)泰安訊近日,山東省市場(chǎng)監(jiān)管局公布了省級(jí)質(zhì)量基礎(chǔ)設(shè)施助力產(chǎn)業(yè)鏈供應(yīng)鏈質(zhì)量聯(lián)動(dòng)提升試點(diǎn)項(xiàng)目名單,泰安市礦山裝備及工程...[詳細(xì)]
- 大眾日?qǐng)?bào) 2024-09-10
煙臺(tái)市奇山醫(yī)院舉行質(zhì)量持續(xù)改進(jìn)項(xiàng)目競(jìng)賽
- 水母網(wǎng)9月5日訊為積極響應(yīng)國(guó)家“關(guān)于加強(qiáng)醫(yī)療質(zhì)量管理、推動(dòng)醫(yī)療服務(wù)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號(hào)召,深化醫(yī)院內(nèi)部管理、激發(fā)員工創(chuàng)新活力、提升醫(yī)療服...[詳細(xì)]
- 水母網(wǎng) 2024-09-10
棗莊提升教育服務(wù)保障水平
- 去年10月7日是米山頂村的娃娃們第一次坐上校車(chē)的日子。如今,越來(lái)越多的山區(qū)娃娃們實(shí)現(xiàn)了從“家門(mén)口”到“校門(mén)口”安全無(wú)縫銜接。今年,38...[詳細(xì)]
- 大眾日?qǐng)?bào) 2024-09-10
濟(jì)南起步區(qū)與山東鐵投集團(tuán)簽約
- □記者劉飛躍報(bào)道本報(bào)濟(jì)南訊近日,濟(jì)南新舊動(dòng)能轉(zhuǎn)換起步區(qū)管委會(huì)與山東鐵投集團(tuán)舉辦《山東鐵投智能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產(chǎn)業(yè)合作項(xiàng)目戰(zhàn)略合作協(xié)...[詳細(xì)]
- 大眾日?qǐng)?bào) 2024-09-10
菏澤市城鄉(xiāng)居民基本醫(yī)保繳費(fèi)方式
- 一、微信小程序繳費(fèi) 微信搜索“山東稅務(wù)社保費(fèi)繳納”;點(diǎn)擊“實(shí)名認(rèn)證”,點(diǎn)擊“實(shí)名”-“授權(quán)同意”,輸入“微信支付密碼”進(jìn)行實(shí)名認(rèn)證;...[詳細(xì)]
- 牡丹晚報(bào) 2024-09-10
大國(guó)重器帶你走近“新”山東
- □大眾新聞?dòng)浾哽枈檹堊恿祭顨J鑫謝巨洋申家鑫“剛下線(xiàn)的盾構(gòu)機(jī),就讓我第一時(shí)間見(jiàn)識(shí)了。”“看完直播就想去。近期,“大眾”新媒體大平臺(tái)推...[詳細(xì)]
- 大眾日?qǐng)?bào) 2024-09-10
12313熱線(xiàn)山東分中心持續(xù)深化管理工作架好為民服務(wù)連心橋
- 本報(bào)濟(jì)南訊近期,12313熱線(xiàn)山東分中心采取扎實(shí)舉措,持續(xù)深化熱線(xiàn)管理工作,切實(shí)回應(yīng)群眾關(guān)切,架好為民服務(wù)連心橋。將人才培養(yǎng)作為提升熱...[詳細(xì)]
- 東方煙草報(bào)·山東視窗 2024-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