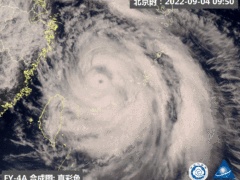中國法學的十字街頭
來源:法治日報
2022-09-07 09:50:09
原標題:中國法學的十字街頭
來源:法治日報
□ 余定宇
孔子所生活的那個“春秋”年代,諸侯爭霸、天下大亂。當此之時,有許多知識分子,亦紛紛懷著一腔“以天下為己任”的熱血,挺身而出尋求各種各樣的“治國之道”。于是,中國法律思想史的發展軌跡,便開始從昔日的中原大地,轉向了泰山腳下的山東。
在這片昔日的“齊魯大地”之上,先是有儒家的孔子出來主張“無訟”、倡言“復禮”,繼而,又有墨家的墨子起來力言“非攻”“法天”“法儀”(即提倡自然正義),接著,更有孟子高揚“民本”“民權”的旗幟,勇敢地發出了一聲“民為貴,君為輕”的吶喊。這邊廂,當道家的老子、莊子在嬉笑怒罵、辛辣諷刺一切統治階級的“實在法”時,那邊廂,那位力倡“性惡論”的儒家新秀荀子卻又在大聲地呼喚著“圣人之治”。不過此時,在荀子主持的“稷下學宮”里,忽然又后院起火,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等一大批自由派思想家們,在黃帝的“王道主義”和老子“道法自然”“無為而治”學說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一門風靡一時的“黃老學派”,力言執政者要“抱道執度”“約法恤刑”。
平心而論,這個時候的中國法律思想史,真的是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活躍、學術繁榮的“黃金時期”。毋庸諱言:中國法律史傳統,正面臨著兩種政治——“賢人政治”與“官僚政治”生死決斗的時刻。只有孔子的儒家學說,雖然在秦始皇時代亦曾飽受“焚書坑儒”的迫害,但在西漢初期以后,又終能死灰復燃,不僅成為“百家爭鳴”最后的勝利者,而且,還在日后幾千年的專制時代里,被歷代的帝王們尊奉為中國官方法律思想的正統。
孔子的思想,其實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之言,它絕不是唯一的并能代表終極真理的一家。毫無疑問,在“個人道德修養”方面,孔學有著極其博大精深的一面;而同樣毋庸置疑的是:在“治國之道”方面,他一直都以為,中國只要回到“周禮”的軌道上去,就一定會天下太平。西周的“禮治”,其實質是一種“德治”與“法治”的混合。而周公所提倡的那種“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則顯示出周公對司法制度“公平正義”的高度重視,和一種對“依法治國”的“治國之道”的深刻認識。而與孔子同時期的老子,更隱隱約約地提出了一種“道在德之上”、要“依道治國”的全新主張。但孔子卻對周公、老子這些散發著強烈“法治”意味的思想學說視而不見,一味地談一個“德”字,或談一個“仁”字。
孔子一生極端地推崇“德治”,而極端地貶低“法治”,更遑論他根本不思考“道治”。例如,他曾經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又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已經把法律視為一件不道德的事,進而不承認法律、否認司法制度的必要性了。從學理上來說,倫理道德,只是一種涵養自己思想品質的修心養性之學;而法律法規,則是一種調節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關系的社會科學。這二者都各有其使用范圍和適用對象,都不可偏廢,亦切不可錯位。但終其一生,孔子卻始終都堅持著這樣的一種天真信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然而這種單純依靠“君子”來教化“小人”的治國理念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德說教,是否真的靠得住呢?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
當然,在今日西方許多國家里,亦曾經出現過一些“權利濫用”“官司濫訟”的不良現象,因此,在西方,孔子主張的“無訟”思想,便越來越受到許多當代法學家們的重視。而孔學的核心思想——“仁”字,也曾經被翻譯成“良心”一詞(conscience),直接寫入聯合國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之中,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偉大格言,也被鐫刻在聯合國大樓的墻壁之上。但在中國,有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卻是:孔夫子的“無訟主義”,在西漢以后,被歷朝歷代的封建帝王接了過去,加以狡猾而巧妙地改造發揮。于是,在歷史上的中國,法律和法學,便徹底地淪為了政治的附庸,而漸漸地喪失了自己原先就不那么豐滿的“獨立和公正”的品格。
(文章節選自余定宇《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神獸到“六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頂級體操賽事緣何花落魯西北小城
- 8月8日至15日,2022年“體總杯”全國體操團體錦標賽在山東德州樂陵舉辦。包括奧運冠軍鄒敬園、劉洋等在內的國家體操隊全體隊員,以及來自各...[詳細]
- 光明網山東頻道 2022-09-07
山東:社區文化建設迎來更多“合身服務”
- 近兩年,山東重點關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社區末梢,在深入調研基礎上,圍繞群眾特定需求,創新開展服務,取得階段性成效。家住濟南市槐蔭區...[詳細]
- 中國文化報 2022-09-07
養成教育 打通立德樹人“最后一公里”
- 遵循“素質是養成的”這一規律,學校全面實施大學生養成教育,拓寬思想政治教育渠道,打通立德樹人“最后一公里”。“類別+項目”構建大學...[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2-09-07
政府搭臺破局 推動產教融合提速
- 產教融合作為類型教育的典型標志,對職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開放后,職業學校主要由行業企業舉辦,面向產業崗位需要定向培養學生,...[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2-09-07
校園手機管理要剛柔相濟
- 據極目新聞報道,9月2日,秦皇島一所中學在學生報到時,將一把錘子和一張紙擺放在校門口的桌子上。紙上印著“免費碎手機”,表示學生如果偷...[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2-09-07
都市麗人門店擴張業績顯著提升
- 2022年中報顯示,上半年都市麗人營收16.18億元,歸母凈利潤1012.3萬元;在成本管控方面,銷售及營銷費用同比減少約12.8%,一般及行政費用同...[詳細]
- 中華工商時報 2022-09-07
中超第16輪北京國安戰平浙江隊
- 本報訊在9月6日進行的2022賽季中超第16輪比賽中,在山東日照坐鎮主場的北京國安2比2與浙江隊戰平。這位荷蘭教練接手球隊時間不長,讓球隊在...[詳細]
- 中國體育報 2022-09-07
林書豪加盟廣州 馬尚回歸廣東
- 本報訊9月5日,廣州男籃發布公告,表示已與外援林書豪完成簽約,新賽季林書豪將身披7號球衣代表球隊參加CBA聯賽。廣東男籃于9月6日也發布公...[詳細]
- 中國體育報 2022-09-07
中國國象甲級聯賽重慶開幕
- 本報訊“武陵山大裂谷杯”中國國際象棋甲級聯賽9月6日在重慶涪陵揭開戰幕。在常規賽首輪慢棋賽中,丁立人領銜的浙江紹興越城隊以2.5比2.5戰...[詳細]
- 中國體育報 2022-09-07
“真切感受到中國領導人的為民情懷”(大道之行)
-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英國青年卡梅隆·詹姆斯·帕特森剛剛以助理教師的身份加入蘭卡斯特大學孔子學院。他操著一口流利的中文高興地說 “在...[詳細]
- 人民日報 2022-09-07
在發掘中保護 在利用中傳承(美麗中國)
- 核心閱讀近年來,我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不斷推進,各地積極探索文化遺產中的生態價值,科學開發生態產業化發展模式,努力讓農業文化遺產...[詳細]
- 人民日報 2022-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