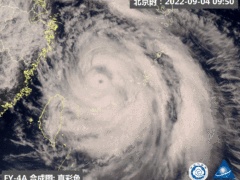鄉(xiāng)土、現(xiàn)實(shí)和詩(shī)性
來(lái)源:中國(guó)文化報(bào)
2022-09-08 09:15:09
原標(biāo)題:鄉(xiāng)土、現(xiàn)實(shí)和詩(shī)性
來(lái)源:中國(guó)文化報(bào)
顏全毅
戲劇也被稱(chēng)為“劇詩(shī)”,高度假定化的時(shí)空設(shè)定與戲劇規(guī)律的束縛,使得戲劇在演繹現(xiàn)實(shí)生活時(shí),與影視、小說(shuō)有著大相徑庭的表現(xiàn)手法,抽象和寫(xiě)意的舞臺(tái)美學(xué),則讓很多觀眾認(rèn)可并期待舞臺(tái)劇區(qū)別于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藝術(shù)手段。不過(guò),現(xiàn)實(shí)題材的當(dāng)下性、鄉(xiāng)土生活的現(xiàn)實(shí)感,又使得戲劇舞臺(tái)上的農(nóng)村現(xiàn)實(shí)題材劇目比起歷史劇、年代劇以及更多的傳奇作品更容易以直截了當(dāng)?shù)默F(xiàn)實(shí)手法貼近觀眾,與現(xiàn)實(shí)的急迫粘連又容易流失戲劇詩(shī)意的表達(dá),這也是許多戲劇創(chuàng)作者頗覺(jué)遺憾的問(wèn)題。在大量的實(shí)踐和探索之后,在第十三屆中國(guó)藝術(shù)節(jié)這樣全國(guó)性高水準(zhǔn)平臺(tái)上,我們可以看到近些年一些現(xiàn)實(shí)農(nóng)村題材劇目,在粗糲樸素的現(xiàn)實(shí)語(yǔ)境書(shū)寫(xiě)中,嘗試找到屬于戲劇舞臺(tái)特有的詩(shī)性語(yǔ)匯,為中國(guó)鄉(xiāng)土大地上眾多平民,勾勒刻畫(huà)出一種時(shí)代圖譜和普遍心性,給當(dāng)代舞臺(tái)增添了一些亮色。
“詩(shī)性”的尋求與表達(dá),首先是不甘于矛盾沖突的簡(jiǎn)單對(duì)立化,以一般起承轉(zhuǎn)合講述故事而放棄歷史與現(xiàn)實(shí)意味,努力更全面立體化地勾勒出現(xiàn)實(shí)中鄉(xiāng)土百姓的生存境況與心靈圖景,以之勾連歷史和現(xiàn)實(shí),帶有更深沉的人文解讀。例如本次藝術(shù)節(jié)演出的話(huà)劇《八步沙》,取材于甘肅古浪縣六位老漢治沙植樹(shù)的真實(shí)事跡,“八步沙”實(shí)有其地,位于河西走廊咽喉地帶,是騰格里沙漠南緣凸起的一片沙漠。1982年,古浪縣的郭朝明、賀發(fā)林等六位須發(fā)皆白的老漢,按下紅手印,開(kāi)始治沙植樹(shù)的艱難歷程。以六老漢為始,三代人前仆后繼、付出至今,讓八步沙荒漠變林場(chǎng),煥然一新。比起一般戲劇敘述,《八步沙》沒(méi)有追求跌宕豐富的人物沖突、情感糾葛寫(xiě)法,更多著筆的是人與自然的矛盾,以及在這巨大矛盾前人類(lèi)改造自然的虔敬與辛勞,將個(gè)別人的奮斗升華為特殊時(shí)期、特殊區(qū)域,鄉(xiāng)村百姓改變生存困境的不凡意志,具有強(qiáng)烈時(shí)代意味和激勵(lì)色彩的人類(lèi)共情。青島歌劇《馬向陽(yáng)下鄉(xiāng)記》則以夸張的喜劇化的手段,將扶貧書(shū)記馬向陽(yáng)下鄉(xiāng)遭遇的當(dāng)代農(nóng)村生活困境與不懈改變的精神,以“喜歌劇”的定位予以體現(xiàn)。話(huà)劇《柳青》講述陜西作家柳青為創(chuàng)作反映農(nóng)業(yè)合作化時(shí)期廣大農(nóng)民在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走社會(huì)主義道路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創(chuàng)業(yè)史》,毅然放棄大城市優(yōu)渥的生活條件,并辭去縣委副書(shū)記職務(wù),舉家搬遷到長(zhǎng)安縣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戲劇既實(shí)又虛,一方面表現(xiàn)柳青所面對(duì)的新中國(guó)成立之初社會(huì)主義農(nóng)村嶄新變化的環(huán)境與農(nóng)民樣貌,這是真實(shí)厚重的歷史真實(shí);另一方面,是后來(lái)呈現(xiàn)在《創(chuàng)業(yè)史》小說(shuō)中的重要人物,王三老漢、王家斌、劉遠(yuǎn)福、郭安成、彩霞、雪娥等都出現(xiàn)在舞臺(tái)上,小說(shuō)的典型化與當(dāng)代鄉(xiāng)村的真實(shí)人物以戲劇化的手法結(jié)合在一起,呈現(xiàn)出歷史與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與舞臺(tái)交相輝映的詩(shī)意化氣質(zhì)。
與《柳青》題材類(lèi)似,第十三屆中國(guó)藝術(shù)節(jié)參評(píng)的新劇目——湖南花鼓戲《山那邊人家》也是以作家入戲,勾連起新中國(guó)農(nóng)村一個(gè)特殊時(shí)期的生動(dòng)場(chǎng)景和人物群像。湖南益陽(yáng)籍作家周立波于1954年底從北京回到故鄉(xiāng),在此后長(zhǎng)達(dá)二十五年的故鄉(xiāng)生活與體驗(yàn),使他的“回鄉(xiāng)敘述”系列短篇小說(shuō),充滿(mǎn)了淳樸與簡(jiǎn)練的風(fēng)格。戲劇選取了周立波系列短篇小說(shuō)《山那邊人家》《禾場(chǎng)上》《桐花沒(méi)有開(kāi)》《掃盲志異》等,融合貫通為一出完整大戲,“婚禮”“泡種”“禾場(chǎng)上”“掃盲志異”“臘月”五場(chǎng)戲別出心裁,和現(xiàn)當(dāng)代戲曲“一人一事”起承轉(zhuǎn)合的結(jié)構(gòu)迥然有異,沒(méi)有核心沖突事件,沒(méi)有對(duì)立人物,宛如散文小詩(shī),以周立波的視角,串連起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huì)進(jìn)入社會(huì)主義時(shí)期發(fā)生的從現(xiàn)實(shí)到心理的巨大轉(zhuǎn)變。花鼓戲《山那邊人家》巧妙之處在于,不是以疾風(fēng)驟雨的沖突去寫(xiě)鄉(xiāng)村現(xiàn)實(shí)之“變”——這本是戲劇擅長(zhǎng)的表現(xiàn)手法,卻以涓涓細(xì)流般的敘述風(fēng)格呈現(xiàn)出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shí)共同作用下農(nóng)村生活和人心的“漸變”:一場(chǎng)婚禮,帶有古來(lái)有之的傳統(tǒng)習(xí)俗,偏偏有來(lái)賓大談國(guó)際形勢(shì),古今交融、中西合璧,令人莞爾;何家翁媽操心女兒的婚事,雖然進(jìn)入新的時(shí)代,她和眾堂客也依舊帶有不由分說(shuō)“父母之命”的家長(zhǎng)式作風(fēng),而濃墨重彩的鄉(xiāng)村老漢鄧滿(mǎn)爹,他的能干與霸道,對(duì)兒子的慈愛(ài)與不講理,對(duì)媳婦的欣賞與猜忌,都在戲劇提供的“漸變”背景下,演繹出更為生動(dòng)和厚實(shí)的時(shí)代圖景。“散文詩(shī)”的獨(dú)特表達(dá)手法,讓《山那邊人家》成為近年來(lái)現(xiàn)實(shí)農(nóng)村題材戲劇創(chuàng)作中令人過(guò)目難忘的作品。
然而在另外一面,戲劇“詩(shī)性”的表達(dá)絕非易事,對(duì)創(chuàng)作者而言更有如走鋼絲般的難度,是要吃透舞臺(tái)、劇種和題材特色后的綜合考量。畢竟,如同英國(guó)戲劇家阿契爾所說(shuō)的,戲劇的實(shí)質(zhì)是“激變”,急遽發(fā)展的沖突與改變,往往推動(dòng)著戲劇的節(jié)奏變化,只有“詩(shī)意”的提煉,較難吸引觀眾的全神貫注。特別是戲劇高潮的推動(dòng)發(fā)展,極為考驗(yàn)編劇與二度創(chuàng)作的水準(zhǔn)。即以《八步沙》《馬向陽(yáng)下鄉(xiāng)記》《山那邊人家》三劇的高潮段落設(shè)計(jì)來(lái)看,也有對(duì)“詩(shī)性”追求不同的處理。
話(huà)劇《八步沙》是對(duì)厚重現(xiàn)實(shí)的史詩(shī)化升華,六個(gè)農(nóng)民治沙種樹(shù),不再是以往“人定勝天”的豪邁宣告,而是人在殘酷自然環(huán)境下不斷探索生存與生機(jī)的“不放棄”精神的寫(xiě)照。高潮起于更具殺傷力的一場(chǎng)沙塵暴,劇中鄉(xiāng)村遭遇了更大危機(jī),反過(guò)來(lái)印證著農(nóng)民治沙事業(yè)艱難卻必然的邏輯因果,三代人治沙因而有了悲壯而動(dòng)人的現(xiàn)實(shí)必然。歌劇《馬向陽(yáng)下鄉(xiāng)記》則在高潮設(shè)置上放棄詩(shī)化處理而轉(zhuǎn)向激烈的事件沖突:馬向陽(yáng)回到大槐樹(shù)村當(dāng)?shù)谝粫?shū)記,先前面對(duì)的矛盾如村民的小農(nóng)意識(shí)、傳統(tǒng)宗族勢(shì)力以及原有村干部工作失誤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后一個(gè)商人覬覦村里的大槐樹(shù),買(mǎi)通原來(lái)的村支書(shū)和部分村民,要遷移走這棵千年大樹(shù),波瀾興起。為保護(hù)生態(tài)文明,馬向陽(yáng)和現(xiàn)任村支書(shū)李元芳不顧一切捍衛(wèi)大樹(shù),歌劇詠嘆調(diào)由此生發(fā)。《馬向陽(yáng)下鄉(xiāng)記》的高潮沖突是激烈的,但也與全劇輕喜劇詩(shī)意風(fēng)格有了一定出入,人為設(shè)置痕跡較為明顯。
湖南花鼓戲《山那邊人家》高潮設(shè)置則一反套路、獨(dú)出機(jī)杼。全劇按照四季農(nóng)時(shí)設(shè)定場(chǎng)次,最后的《殺年豬》,是一年農(nóng)業(yè)耕耘的結(jié)束,更是新春開(kāi)啟的序幕,劇中沒(méi)有不同動(dòng)機(jī)人物之間的爭(zhēng)吵爭(zhēng)斗,沒(méi)有是非曲直的較量折沖,高潮起于主人公伏生夫妻在小山村里所做的一個(gè)驚人決定:將這一年辛苦喂養(yǎng)的豬,殺后分發(fā)給全村的鄉(xiāng)民。這個(gè)“分豬肉”的事件說(shuō)小實(shí)大,是在千百年小農(nóng)辛苦耕耘、閉門(mén)小戶(hù)傳統(tǒng)向農(nóng)村合作社跨進(jìn)的一次實(shí)際行動(dòng),是經(jīng)歷了“泡種事件”“掃盲事件”等諸多新舊文化心理碰撞后,山鄉(xiāng)農(nóng)民對(duì)新社會(huì)、新文化的積極響應(yīng)與自覺(jué)認(rèn)同。編劇在整劇惜墨如金,少有恣肆情感流露的克制下,卻在“分豬肉”時(shí),不惜一一點(diǎn)出分豬肉每個(gè)村民的名字,以及每個(gè)村民此時(shí)臉上與內(nèi)心細(xì)微獨(dú)到的變化。戲劇的張力總是在于草蛇灰線(xiàn)和起伏綿延,前場(chǎng)中女主人公胡桂花辛勤喂豬后的美好設(shè)想:為滿(mǎn)爹買(mǎi)一雙干部帽子,為丈夫置換一身新式中山裝,也為自己買(mǎi)一個(gè)看中已久的彩色發(fā)卡,此時(shí)成為牽動(dòng)觀眾的核心懸念,當(dāng)山村旁觀者、記錄者周立波適當(dāng)其時(shí)地把自費(fèi)購(gòu)買(mǎi)的發(fā)卡遞到了桂花手中時(shí),情感高潮迅速而準(zhǔn)確地?fù)糁杏^眾。毫無(wú)疑問(wèn),這樣高潮的反常態(tài)設(shè)置,既是傳統(tǒng)戲曲豐富手段的高明借鑒,也是作者富有勇氣的自我挑戰(zhàn)。《山那邊人家》結(jié)尾寓意十足:一個(gè)小小事件,把千百年耕織在鄉(xiāng)村的農(nóng)民的自我破解開(kāi),展現(xiàn)出對(duì)未來(lái)社會(huì)主義新社會(huì)的無(wú)限期許;雖然滿(mǎn)爹的帽子、伏生的中山裝沒(méi)有了,一個(gè)發(fā)卡,卻讓“公”與“私”不可分割的細(xì)密關(guān)系,悲喜交錯(cuò)、張力十足地呈現(xiàn)于舞臺(tái),真實(shí)細(xì)膩地演繹出社會(huì)文明巨大跨越下,鄉(xiāng)土生活的時(shí)代變遷,這就是一種“詩(shī)性”的戲劇意味。
想爆料?請(qǐng)登錄《陽(yáng)光連線(xiàn)》(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xiàn)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xiàn)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xiàn)0531-81695052,誠(chéng)邀合作伙伴。
?舞出老百姓的文化底氣
- 融入時(shí)代元素,讓傳統(tǒng)民俗煥發(fā)出新的活力。《擺出一個(gè)春天》取材于云南省普洱市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拉祜族傳統(tǒng)民間舞蹈“擺舞”,融入拉祜族《...[詳細(xì)]
- 中國(guó)文化報(bào) 2022-09-08
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寶藏
-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一座無(wú)價(jià)的寶藏,蘊(yùn)含著豐富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guī)范等優(yōu)秀內(nèi)容。新時(shí)代要傳承弘揚(yáng)這些優(yōu)秀內(nèi)容,激活中華優(yōu)秀傳...[詳細(xì)]
- 光明日?qǐng)?bào) 2022-09-08
擔(dān)當(dāng)作為,是他們最閃亮的名片
- 不久前,全國(guó)司法行政系統(tǒng)先進(jìn)模范表彰大會(huì)在京舉行。??“我們社區(qū)有居民1800多戶(hù),130個(gè)門(mén)棟、7個(gè)網(wǎng)格,每個(gè)門(mén)棟長(zhǎng)都是信息員,網(wǎng)格員則...[詳細(xì)]
- 光明日?qǐng)?bào) 2022-09-08
提升文明坐標(biāo) 引領(lǐng)美好風(fēng)尚
- 【百姓身邊看文明】????在山東省濟(jì)南市歷下區(qū)的泉城路街道,既有濟(jì)南最繁華的商業(yè)步行街,又能看到“家家泉水、戶(hù)戶(hù)垂楊”的美好景象,...[詳細(xì)]
- 光明日?qǐng)?bào) 2022-09-08
樓宇經(jīng)濟(jì)比拼區(qū)域競(jìng)爭(zhēng)新優(yōu)勢(shì)
- 日前,2022服貿(mào)會(huì)·中國(guó)樓宇經(jīng)濟(jì)北京論壇舉行。世界貿(mào)易網(wǎng)點(diǎn)聯(lián)盟主席布魯諾·麥斯?fàn)枴⑸虅?wù)部原副部長(zhǎng)魏建國(guó)、全聯(lián)房地產(chǎn)商會(huì)秘書(shū)長(zhǎng)趙正挺、...[詳細(xì)]
- 中華工商時(shí)報(bào) 2022-09-08
海軍航空兵發(fā)展論壇聚焦實(shí)戰(zhàn)展望未來(lái)
- 本報(bào)青島9月7日電記者錢(qián)曉虎、通訊員楊潔瑜報(bào)道 在海軍航空兵成立70周年之際,海軍于9月6日至7日,在海軍航空大學(xué)青島校區(qū)舉辦海軍航空兵發(fā)...[詳細(xì)]
- 解放軍報(bào) 2022-09-08
勇立潮頭馳騁萬(wàn)里海疆
- 南海某海域,海軍山東艦如開(kāi)山巨斧,劃開(kāi)一望無(wú)際的深藍(lán)海面。正是在這艘巨艦上,在這些戰(zhàn)機(jī)旁,他迎來(lái)了人生的“高光時(shí)刻”——2019年12月...[詳細(xì)]
- 解放軍報(bào) 2022-09-08
建“南繁硅谷” 強(qiáng)“種業(yè)芯片”(新氣象 新作為)
- 2022年4月,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海南考察時(shí)指出 “我一直關(guān)注南繁科研育種,要科學(xué)謀劃加快推進(jìn),建設(shè)成服務(wù)全國(guó)的南繁硅谷。近年來(lái),海南發(fā)揮自...[詳細(xì)]
- 人民日?qǐng)?bào)海外版 2022-09-08
“智慧的車(chē)”迎來(lái)快速發(fā)展期
- 不僅有“智慧的車(chē)”,還有“聰明的路”“協(xié)同的云”——服貿(mào)會(huì)充分展現(xiàn)了中國(guó)智能網(wǎng)聯(lián)汽車(chē)領(lǐng)域的新趨勢(shì)、新突破。工業(yè)和信息化部最新數(shù)據(jù)顯...[詳細(xì)]
- 人民日?qǐng)?bào)海外版 2022-09-08
立足崗位作貢獻(xiàn) 真抓實(shí)干創(chuàng)佳績(jī)(喜迎二十大)
- 黨的二十大即將召開(kāi)的喜訊傳來(lái),各地干部群眾滿(mǎn)懷期待,紛紛表示要立足崗位作貢獻(xiàn)、真抓實(shí)干創(chuàng)佳績(jī),以實(shí)際行動(dòng)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kāi)。”...[詳細(xì)]
- 人民日?qǐng)?bào)海外版 2022-09-08
南京郵電大學(xué):在田間地頭上好“大思政課”
- 帶著孩子們上一堂“暑期預(yù)防溺水”主題的美術(shù)課,為農(nóng)村描繪色彩斑斕的墻面,帶領(lǐng)中小學(xué)生參觀自動(dòng)化蘭花養(yǎng)育大棚,體驗(yàn)鄉(xiāng)村振興的發(fā)展成果...[詳細(xì)]
- 中國(guó)青年報(bào) 2022-09-08
全國(guó)縣域共青團(tuán)基層組織改革全面推開(kāi)
- 黨的十八大以來(lái),以習(xí)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青年和共青團(tuán)工作,親自指導(dǎo)推動(dòng)共青團(tuán)改革,特別是對(duì)加強(qiáng)團(tuán)的基層建設(shè)作出一系列重要...[詳細(xì)]
- 中國(guó)青年報(bào) 2022-09-08
提高黨團(tuán)隊(duì)一體化育人質(zhì)量 奮力推動(dòng)新時(shí)代山東少先隊(duì)工作走在前開(kāi)新局
- 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慶祝中國(guó)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tuán)成立100周年大會(huì)上強(qiáng)調(diào),“在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征程上,中國(guó)共產(chǎn)黨是先鋒隊(duì),共青團(tuán)是突擊隊(duì),...[詳細(xì)]
- 中國(guó)青年報(bào) 2022-09-08
- 9月6日0時(shí)至12時(shí)青島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情況
- 2022年9月6日0時(shí)至12時(shí)青島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情況
- 山東省第25屆運(yùn)動(dòng)會(huì)各項(xiàng)賽事圓滿(mǎn)完成 青島、濟(jì)南、淄博分列獎(jiǎng)牌榜前三
- 百度地圖發(fā)布2022中秋出行預(yù)測(cè):煙臺(tái)蓬萊閣景區(qū)或成熱門(mén)旅游地 濟(jì)南入榜“文藝之城” 青島入榜“美食之城”
- 記者探訪(fǎng):濟(jì)南海鮮市場(chǎng)梭子蟹85元一斤 中秋預(yù)計(jì)100元 節(jié)后將會(huì)降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