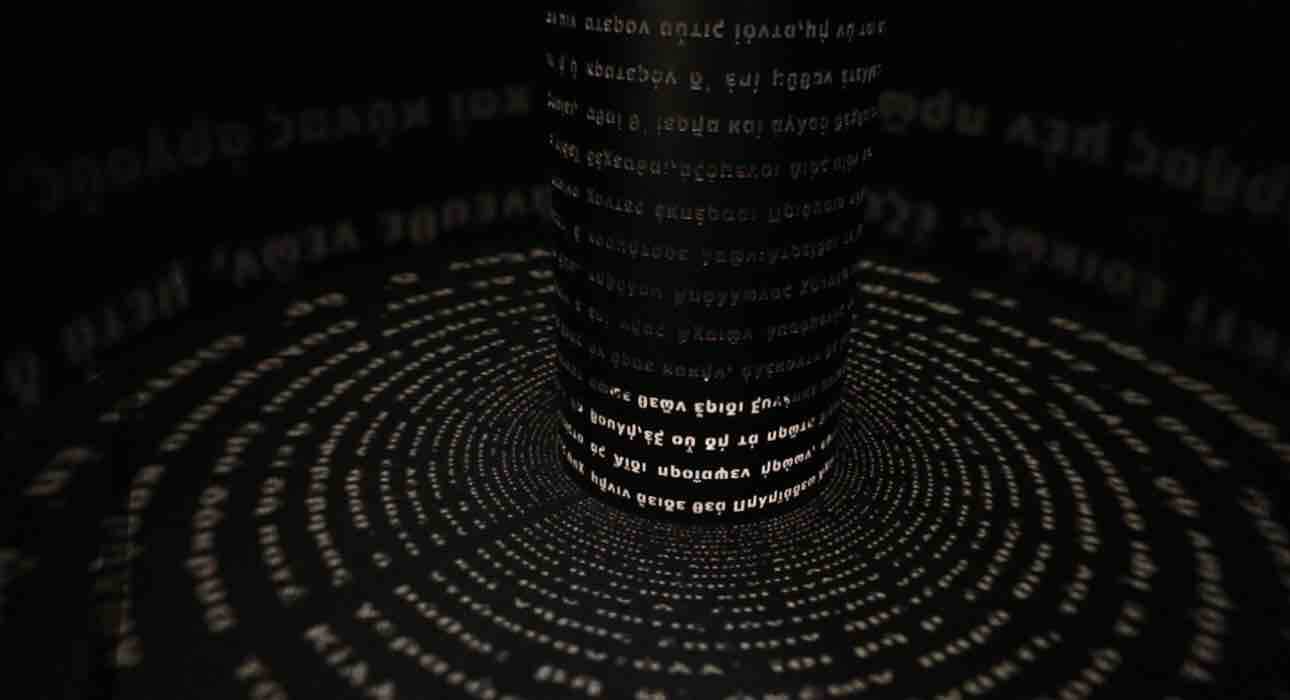“慎終追遠(yuǎn)”及其現(xiàn)代價(jià)值
來源:光明日?qǐng)?bào)
2023-04-01 13:12:04
原標(biāo)題:“慎終追遠(yuǎn)”及其現(xiàn)代價(jià)值
來源:光明日?qǐng)?bào)
原標(biāo)題:“慎終追遠(yuǎn)”及其現(xiàn)代價(jià)值
來源:光明日?qǐng)?bào)
養(yǎng)親、敬親、諫親和慎終追遠(yuǎn),構(gòu)成了儒家孝道的基本內(nèi)涵。朱熹認(rèn)為孝是發(fā)用,仁是本體,孝是仁本在父子倫理上的自然顯現(xiàn)。猶如萬(wàn)里黃河綿延流長(zhǎng),一路要流經(jīng)許多湖泊,孝就是黃河流經(jīng)的第一個(gè)“水塘子”。曾子是孔子孝道的傳承者。根據(jù)《史記》《漢書》記載,《孝經(jīng)》即由孔子講授、曾子及其弟子撰而成書。“慎終追遠(yuǎn)”就出自曾子之口。“慎終”是指按照喪禮慎重辦理父母喪事;“追遠(yuǎn)”指春秋祭祀,以示懷念追思祖先。“慎終”與“追遠(yuǎn)”,是孝道社會(huì)化儀式的兩大原則。
“慎終”貴在有真情
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yǔ)·為政》)曾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孟子·滕文公上》)這兩段話觀點(diǎn)一致,文字也雷同。不僅要以禮“事生”,也要以禮“事死”。讓活著的人,活得要有尊嚴(yán);當(dāng)一個(gè)人告別人世,這種告別儀式也必須有莊重感。“事之以禮”是對(duì)生者的尊重,“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對(duì)逝者的尊重。《孟子·滕文公上》記載了一則故事:一位男子的父親去世,此人將其父親尸體扔在山溝里。有一天此人路過山溝,發(fā)現(xiàn)狐貍在啃食其父的尸體,蒼蠅蚊蟲不停地叮咬尸體。這位男子頓時(shí)額頭直冒冷汗,眼睛不敢正視。他之所以“睨而不視”,不是表演給別人看,而是內(nèi)心愧疚、悔恨之情的自發(fā)體現(xiàn)。于是馬上掩埋尸體,按照喪葬之禮舉行入葬儀式,心才有所安寧。
孔子雖然非常重視喪祭之禮,但他重視的是在這種禮儀中子女所滋生的內(nèi)在的自然親情,而不是片面追求喪葬之禮外在的周密與繁縟。“喪致乎哀而止。”“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論語(yǔ)·子張》)每個(gè)人在家庭與社會(huì)中的身份不斷變換,每一種身份都有其相應(yīng)的社會(huì)責(zé)任、行為規(guī)范和言行禁忌,人的真情實(shí)感總是隱匿于各種厚重的社會(huì)角色的“盔甲”背后。往往在至親亡故之時(shí),一個(gè)人的真實(shí)情感才會(huì)淋漓盡致地袒露在眾人面前。“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論語(yǔ)·子張》)因此,在喪祭之禮中,孔子強(qiáng)調(diào)的是內(nèi)在自然的悲痛之情、哀思之心。顏回去世時(shí),七十一歲的孔子哭得全身抽搐。學(xué)生勸他不要這么傷心,他說:“我不為這樣的人傷心,還為什么樣的人傷心呢?”“哀”與“敬”二字代表著儒家孝道在喪祭之禮上的觀點(diǎn)。由此而來,只要是發(fā)自內(nèi)在的真情實(shí)意,有一些略顯過激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曾子父親去世,曾子傷心欲絕,“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孔子曾經(jīng)稱贊一位太子的守孝行為:“君薨,聽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滕文公上》)太子為國(guó)君守喪三年,把全部政務(wù)交由冢宰處理,自己每天以稀飯充饑,面色深黑,形銷骨立,天天在靈前哭泣,朝廷官員莫不被太子的哀痛之情感動(dòng)。孔子雖然強(qiáng)調(diào)哀與敬,但是,對(duì)社會(huì)上流行的“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極端自虐自殘的風(fēng)氣多有批評(píng)。孔子認(rèn)為,子女在守喪期間身上長(zhǎng)了膿瘡就應(yīng)該去洗澡,頭頂長(zhǎng)了癤子就應(yīng)該去治療,身體極度虛弱就應(yīng)該吃點(diǎn)補(bǔ)品調(diào)養(yǎng)身體。“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禮記·雜記》)自虐自殘甚至喪失性命,恰恰是不懂“全體貴生”的不孝之舉。
“追遠(yuǎn)”貴在培育感恩之心
孟懿子問孝,孔子回答說:“無(wú)違。”“無(wú)違”是指“無(wú)違禮節(jié)”。孔子之所以非常重視喪祭之禮,原因并不僅僅在于其間滲透著“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孝道精神,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教民追孝”的道德教化作用。“修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禮記·坊記》)郭店楚簡(jiǎn)《六德》也有與孔子思想相吻合的材料:“父子不親,君臣無(wú)義,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劉釗《郭店楚簡(jiǎn)校釋》)
弟子宰予向孔子請(qǐng)教:“子女為何要為父母守孝三年?”他覺得為父母守孝三年的期限太長(zhǎng)了!君子三年不習(xí)禮儀,禮儀就會(huì)荒廢;三年不練習(xí)音樂,音樂就會(huì)失傳。因此想將“三年之喪”縮短為一年。孔子批評(píng)他說:“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想穿新衣服,吃大魚大肉,你這樣做能心安嗎??jī)号瞪旰蟛拍苊撾x父母親的懷抱。替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的通禮。難道你從小就沒有得到父母的慈愛嗎?”師生之間的這一場(chǎng)討論,表面上是在討論古禮“三年之喪”,實(shí)際上涉及感恩這一道德意識(shí)與道德情感如何培植的問題。在孔子看來,“三年之喪”彰顯的不僅是對(duì)父母的孝敬之情,而且也是驗(yàn)證一個(gè)人感恩意識(shí)是否已牢固確立的標(biāo)桿。在倫理學(xué)與心理學(xué)意義上,“感恩”是一種人與動(dòng)物皆有的初始道德意識(shí)。感恩與忠誠(chéng)、公正等是支配人實(shí)現(xiàn)道德行為的思想基礎(chǔ)。因此,孔子對(duì)宰予的批評(píng),表面上是埋怨他不知禮儀,實(shí)際上是批評(píng)宰予感恩之情還沒有真正樹立。感恩事關(guān)靈魂的健康。一個(gè)人心智是否成熟,感恩意識(shí)的培植是一項(xiàng)重要的內(nèi)容。王陽(yáng)明時(shí)常以孝行論證“知行合一”。弟子徐愛問陽(yáng)明:人在知識(shí)上“知得父當(dāng)孝,兄當(dāng)?shù)堋保谌粘I钪型安荒苄ⅲ荒艿堋保@樣知與行如何能合一?王陽(yáng)明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傳習(xí)錄》)王陽(yáng)明以《大學(xué)》“好好色”為例加以說明:“見好色”屬于知,“見”不是中性之見,而是良知之見。不是先“見”了,然后再立一個(gè)“心”來“好色”,而是“見”與“心”同時(shí)呈現(xiàn),不分先后。“好好色”屬于行,行既指外在行為,又包括心理意識(shí)活動(dòng)。我們夸獎(jiǎng)某人是孝子,不是指某人懂得“昏定晨省”的道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誠(chéng)心誠(chéng)意地踐行了孝德。孝并非存在于父母“身上”,而是存在于子女“心上”。舞臺(tái)上的演員表演“溫凊奉養(yǎng)”“昏定晨省”之類孝順父母的節(jié)目催人淚下,時(shí)常贏得觀眾一片喝彩聲。但是,王陽(yáng)明認(rèn)為這僅僅是舞臺(tái)上的表演,演員所表演的孝愛屬于“無(wú)根”之愛。以感恩之心作為孝行的“頭腦”,才是知行合一的孝。緣此,王陽(yáng)明非常重視對(duì)子女與弟子感恩之心的培育。他指出感恩之心的培植必須從兒童教育開始。兒童的特點(diǎn)是“樂嬉游而憚拘檢”,啟蒙教育應(yīng)該像春風(fēng)化雨一般,由淺入深滋潤(rùn)孩子心田。“誘之以歌詩(shī)以發(fā)其志意,導(dǎo)之習(xí)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傳習(xí)錄》)王陽(yáng)明家風(fēng)甚嚴(yán),時(shí)常寫信教育子女“勤讀書,要孝弟”(束景南《王陽(yáng)明年譜長(zhǎng)編》)。在平時(shí)教學(xué)中,他要求弟子每天上課之前必須自我反省四個(gè)問題,第一個(gè)問題是“在家所以愛親敬畏之心,得無(wú)懈忽未能真切否”(《傳習(xí)錄》)。從孔子到王陽(yáng)明,歷代大儒之所以重視感恩之心,原因在于感恩之心的樹立是成就自我、實(shí)現(xiàn)自我的道德基礎(chǔ),王陽(yáng)明稱之為“凡做人,在心地”(束景南《王陽(yáng)明年譜長(zhǎng)編》)。
儒家“慎終追遠(yuǎn)”思想具有深遠(yuǎn)的現(xiàn)代價(jià)值。概而論之,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其一,關(guān)愛生命,尊重父母。“仁者愛人”,讓每一位健在的人活得有尊嚴(yán),而不是茍且偷生;讓每一位逝者離開人世時(shí),告別儀式充滿溫情與友愛。對(duì)逝者的憐憫,是對(duì)生命的尊重。其二,“慎終追遠(yuǎn)”透顯出濃郁的感恩之情。“誰(shuí)言寸草心,報(bào)得三春暉。”自古以來,中華文化非常重視感恩之心,幾乎每一個(gè)傳統(tǒng)節(jié)日都要祭天地、祭先祖,在祭祀儀式中表達(dá)真誠(chéng)的感恩之情。現(xiàn)代社會(huì)出現(xiàn)一些“啃老族”“巨嬰”等不良現(xiàn)象,與感恩教育的缺失有一定的關(guān)系。“誰(shuí)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從文化中國(guó)汲取營(yíng)養(yǎng),是建構(gòu)文化強(qiáng)國(guó)的必由之路。
(作者:曾振宇,系山東大學(xué)儒學(xué)高等研究院教授)
想爆料?請(qǐng)登錄《陽(yáng)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chéng)邀合作伙伴。
展露黃河“無(wú)限風(fēng)光”
- ▲孩子們?cè)邳S河沿線的公園玩耍濟(jì)南市文化和旅游局供圖清風(fēng)3月26日,山東省濟(jì)南市百里黃河風(fēng)景區(qū)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堤壩道路兩側(cè)的紅葉李進(jìn)...[詳細(xì)]
- 中國(guó)文化報(bào) 2023-04-01
紅色熱土上的文旅融合新篇章
- ▲呼和浩特市丁香路小學(xué)黨支部到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jù)地參加黨日活動(dòng),學(xué)習(xí)老一輩革命家的紅色精神。”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jù)地...[詳細(xì)]
- 中國(guó)文化報(bào) 2023-04-01
2023年全國(guó)工會(huì)推進(jìn)全面從嚴(yán)治黨工作會(huì)議召開
- 本報(bào)北京3月31日電(記者鄭莉朱欣)2023年全國(guó)工會(huì)推進(jìn)全面從嚴(yán)治黨工作會(huì)議今天以視頻會(huì)議形式召開。會(huì)議強(qiáng)調(diào),各級(jí)工會(huì)要深入學(xué)習(xí)貫徹習(xí)...[詳細(xì)]
- 工人日?qǐng)?bào) 2023-04-01
9省份實(shí)現(xiàn)惠民殯葬服務(wù)全覆蓋
- 本報(bào)北京3月31日訊(記者敖蓉)在民政部31日舉辦的一季度例行新聞發(fā)布會(huì)上,民政部社會(huì)事務(wù)司副司長(zhǎng)朱玉軍介紹,目前全國(guó)31個(gè)省份和新疆生...[詳細(xì)]
- 經(jīng)濟(jì)日?qǐng)?bào) 2023-04-01
用法治力量護(hù)黃安民
- 黃河,發(fā)源于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北麓,全長(zhǎng)5464公里,跨越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nèi)蒙古、山西、陜西、河南、山東9省區(qū),流域總面積79.5...[詳細(xì)]
- 農(nóng)民日?qǐng)?bào) 2023-04-01
英雄的內(nèi)心世界
- 圖中左起第二是岳飛,第四是張俊,第五是韓世忠,第七是劉光世,四人合稱“中興四將”。清人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記述了岳飛的一方端...[詳細(xì)]
- 檢察日?qǐng)?bào) 2023-04-01
向世界講好牡丹故事 菏澤牡丹國(guó)際傳播論壇將于4月9日舉行
- 日前,記者在相關(guān)部門獲悉,由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中國(guó)外文局主辦的菏澤牡丹國(guó)際傳播論壇,將于4月9日在菏澤會(huì)盟臺(tái)舉行。牡丹國(guó)色天香、雍...[詳細(xì)]
- 光明網(wǎng)山東頻道 2023-04-01
所隊(duì)聯(lián)動(dòng) 數(shù)據(jù)融通 精準(zhǔn)打擊 協(xié)同治理
- 高新區(qū)經(jīng)濟(jì)蓬勃發(fā)展的背后,少不了濟(jì)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經(jīng)濟(jì)犯罪偵查大隊(duì)的保駕護(hù)航。每周一,在高新分局企航云判經(jīng)偵工作室,民警都會(huì)圍坐...[詳細(xì)]
- 人民公安報(bào) 2023-04-01
游出好成績(jī) 展現(xiàn)好狀態(tài)(競(jìng)技觀察)
- 核心閱讀福岡游泳世錦賽和杭州亞運(yùn)會(huì)將于今年陸續(xù)舉辦,為更好完成兩項(xiàng)大賽參賽任務(wù),中國(guó)游泳隊(duì)舉辦兩次選拔賽,即本次全國(guó)春季游泳錦標(biāo)賽...[詳細(xì)]
- 人民日?qǐng)?bào) 2023-04-01

山東青州:花卉產(chǎn)業(yè)“春意”正濃
- 走進(jìn)山東濰坊青州花卉直播電商產(chǎn)業(yè)園,就一腳踩進(jìn)了春天里。18歲的王文旭,像是這條路上一朵待放的蝴蝶蘭。好品盛放,唱響“花品牌”[詳細(xì)]
- 人民網(wǎng)山東頻道 2023-04-01
孩子們變得更陽(yáng)光了身體更棒了
- 前不久,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qū)中小學(xué)生足球聯(lián)賽的賽場(chǎng)上,侯家中學(xué)初一(1)班學(xué)生馬凱如擔(dān)綱前鋒,奔跑、運(yùn)球、過人、射門,拼勁十足。在學(xué)...[詳細(xì)]
- 中國(guó)教育報(bào) 2023-04-01
34個(gè)地區(qū)試點(diǎn)統(tǒng)籌推進(jìn)美德山東和信用山東建設(shè)
- 統(tǒng)籌推進(jìn)美德山東和信用山東建設(shè)現(xiàn)場(chǎng)推進(jìn)會(huì)暨骨干培訓(xùn)班在威海榮成舉辦。按照山東省委、省政府關(guān)于統(tǒng)籌推進(jìn)美德山東和信用山東建設(shè)、實(shí)施全...[詳細(xì)]
- 新華網(wǎng)山東頻道 2023-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