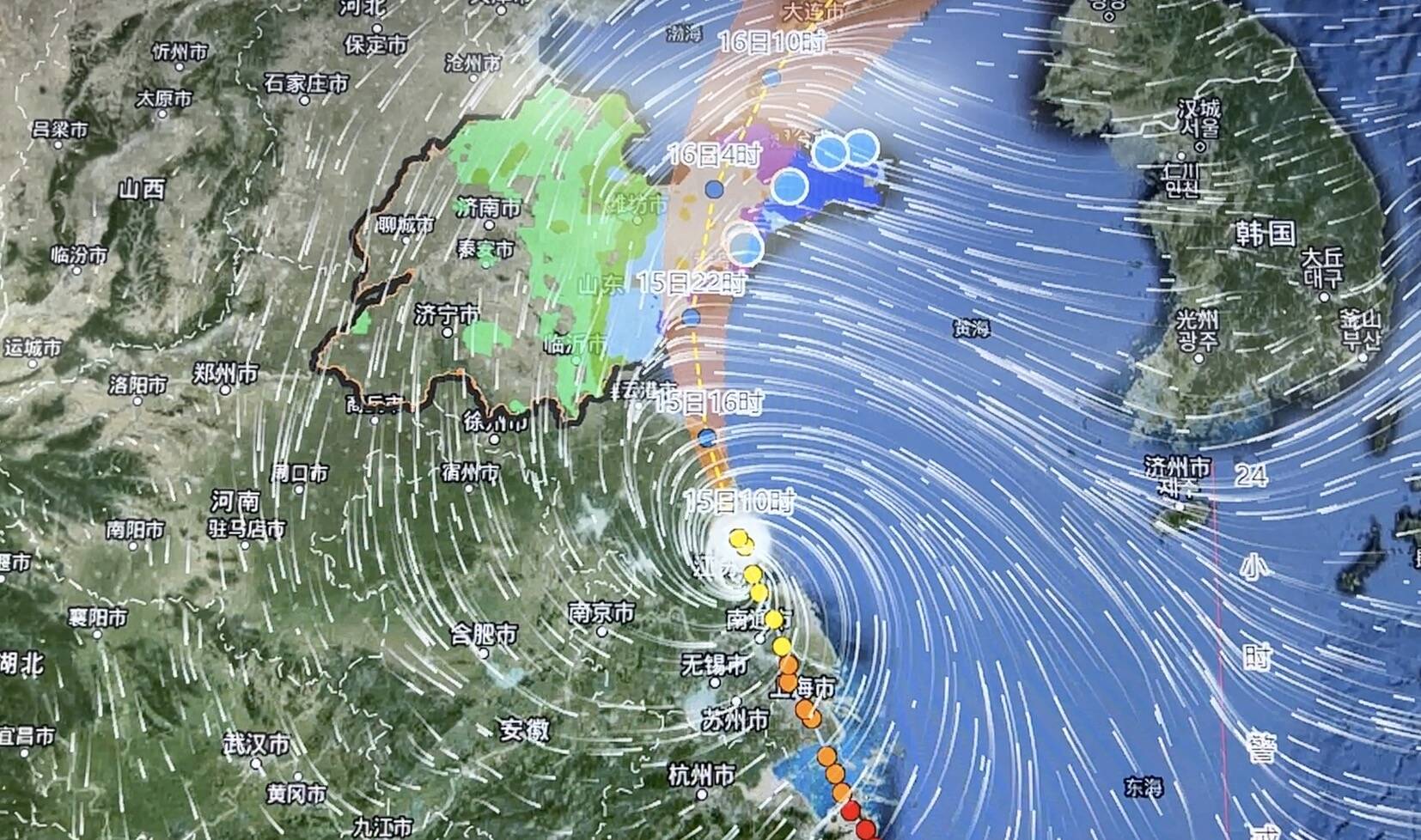稻田紀事
來源:檢察日報
2022-09-18 14:55:09
原標題:稻田紀事
來源:檢察日報
原標題:稻田紀事
來源:檢察日報
水田 王國紅攝影作品
在京城闖蕩二十多年的我,時至今日,與朋友閑聊時會冷不丁脫口而出:“哎哎哎,我是個老農民哎!”語氣中帶著幾分自得。在朋友半信半疑的眼神下,我通常會再提高聲調補上一句:“這是真的,當年我插秧種田的水平可高啦!”
這還真不是吹的。那個“當年”,是指我到京城讀研前的那十多年時間。那時我的父母正當壯年,才四十多歲,幾乎每天從天亮馬不停蹄地忙到天黑,渾身有使不完的力氣。
1.
上小學讀初中時,村里實行的還是集體勞動的生產隊制,小孩子是沒有資格賺工分的,自然不必跟著大人去田里地里干農活。工分是生產隊分糧食的唯一依據,男性全勞力一天記10分,女性一天記6分。為多賺工分,父母申請為生產隊養牛,一頭牛一天加4分。我曾養過一頭大水牛和一頭小母牛。放學后,我的唯一任務是牽牛,年齡大一點的哥哥姐姐則負責割牛草。
1981年,以種水稻為主的家鄉小溪邊開始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下子激發出村民們無限的勞動熱情和高昂的積極性,他們一個個鉚足了勁兒使出渾身解數來經營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當時,我家有六口人,分到的田有三大丘、兩小丘,共3畝8分。哥哥和弟弟的田包括了子孫田,面積比較大,都有一畝多;姐姐和我各一小丘,還不到半畝,剩下的兩丘分給父母。這些田,都不是什么好田。多年后,有一次與媽媽聊天,她感慨地說:“好多時候,眼前的吃虧不一定就真的虧。現在,我們的兩丘田靠近村邊,可以當宅基地建房子,就成寶貝啦。”這是后話。
那時,一年種兩季水稻:早稻與晚稻,外加一季草籽越冬養田。爸爸既勤快又善于學習思考,采用科學方法種田。經過數年的栽種養田,這些田漸漸變成了土壤肥沃的好田,他種的水稻向來都是全村長得最好的,人見人夸!過了幾年,我上了大學,戶口遷走后要多交余糧,好在爸爸種的稻谷收成好,僅溪灘那一小丘的一季早稻就夠全家交余糧了。
剛開始單干那幾年,哥哥都在京城做木匠,長年住在大興。每年春節前一周左右回家過年,元宵節過后出門。每次出門前,都有不少人家到我家商量,希望哥哥能帶著他們的兒子做徒弟。哥哥是家里的榮耀,但家里的農活,他一直干得不多;弟弟才十來歲,正是一日三餐吃飯找不到人的貪玩年紀,也指望不上。因而,每年的“雙搶”,一開始就只有姐姐和我幫父母的忙。全家人月光下種田割稻的場景,是我記憶中最為溫馨的畫面……
每當早稻成熟,放眼田野,金燦燦一片,沉甸甸的稻穗深深地低頭藏在青黃相間的稻葉下。梯田式的田野,一丘高過一丘,大小不一。路邊的水溝里日夜奔流著從水庫里放出來的清水,臨近水溝的稻田,每丘都有一個缺口可以進水。與馬路平行的寬闊田墈是干農活時可以赤腳行走的主干道,自然比上丘與下丘之間的田墈要寬,也更結實。通常情況下,沿主干道生長的青草也更嫰更密,那是讓牛走在水溝里兩邊吃草的好地方。水從高丘流向低丘,而放水是否方便是稻田好差的一個重要標志。
每年放暑假時,我都會算好時間回老家幫著父母干農活。在所有的農活中,對小溪邊的農民來說,我一直認為最苦最累的就是夏季時的“雙搶”。所謂“雙搶”,就是搶收搶種,即收割早稻種下晚稻,必須在半個月內完成,通常時間為7月下旬到8月初立秋前,這也是一年中艷陽高照、酷暑難耐的日子。要是家里的田多,干活的人手少,那絕對是一場披星戴月的苦戰。
我家媽媽呢,凡事追求完美,總希望早稻多留幾天讓每一顆稻穗長得飽滿,出米率高,這樣一來,我家“雙搶”的時間就更短更緊迫。那些年,家中的哥哥常年在外幫不上忙,弟弟又小,主要的幫手就是姐姐和我。關鍵是那段時間每家每戶都忙得熱火朝天,找不到合適的人來幫忙。若是晚稻在立秋后種下,很有可能在沒成熟時就遭遇霜降,導致減產甚至顆粒無收。農民靠天吃飯,對一年二十四節氣特別在意。時令就是農民的律法,一旦違反了,老天爺會讓你承擔嚴重后果。
2.
1985年的夏季“雙搶”,是我記憶中最為深刻的一次。那一年,已出嫁的姐姐隨姐夫包工程去了,家中少了一個得力幫手。我呢,在縣城上了三年省重點高中,剛考完大學回家。無論走到哪兒,鄰居們遇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回家啦,現在畢業了嗎?”接著又問:“大學考上了嗎?”有的更直截了當:“美君,你大學考上啦!”事實上,剛考完試回來還不知道成績的我,到底能考上什么樣的大學,心里也沒底,通常是含含糊糊地應付兩句。從小到大,村民都知道我讀書好,不管最后能上什么樣的大學,在他們眼中都是天大的喜事兒。那時,全村還只出過一位大學生——他叫龐正忠,當年考上西南政法學院,現為京城著名的知識產權律師。
那年暑假,我一邊在家忐忑不安地等待大學錄取通知書,同時為家中的農活出謀劃策,成為父母的最主要幫手。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下,我拔秧種田的技藝進步飛速。
每年“雙搶”開始前,父母都會根據各丘稻子成熟的先后順序作一番統籌安排。晚稻不像早稻只有一個品種,而要分雜交水稻、粳稻、糯稻等,不同品種的生長期也略有不同。我心里有一絲擔憂:一畝多的田,就爸媽和我三人,媽媽通常還要負責翻曬稻谷兼做飯,一天能割完嗎?自己能不能堅持到最后?
清晨5點半,我們就踩著晨曦出發開工了。割稻速度要想快,就要姿勢做到位。爸爸說:兩腳盡量平衡分開,身子前傾彎腰半蹲,從左到右或從右到左,稻稈恰好是一大把,身體重心隨著要割的稻子在兩腳之間作相應的移動,順勢轉身將稻子碼在身后,轉身夠不著時,就換放另一堆,每一堆都必須排列整齊,這樣打稻時拿起來不會散架,打稻機也可直線前移而不必在水田里東彎西拐。我剛割一會兒就渾身汗水濕透、腰酸背疼,若不是看著爸媽年復一年都這么干活,我早就當逃兵了。
出乎意料的是,8點左右回家吃早飯前,我們就將稻子全部割倒碼好了。早飯后,爸爸負責將打稻機打下的稻谷一擔擔挑回操場,由媽媽負責翻曬,媽媽還要做午飯和晚飯,外加下午點心。在挑走稻谷前,爸爸和我先將打稻機拉到一大堆碼好的稻谷邊上,這樣,我一個人時仍可以繼續打稻。說起來,干農活基本上是靠力氣,但也需要動動腦子加上一定的技巧。割稻如此,打稻也不例外。割稻講究姿勢,打稻重在方式。雙手緊捧一把稻子,用盡全身力氣踩動打稻機,待轉盤轉得飛快時,先放垂下的稻頭,慢慢地循序漸進到稻頭根,再翻兩下拉回稻頭,一把稻谷就打得干干凈凈,同時又節省力氣。中途來了表妹君明幫忙,大家鼓足勁兒,在晚上八點半天黑前總算完成了一天的任務。算一算,從早到晚,一天要勞作15個小時左右。
說起來,每年“雙搶”時,全家最發愁的是奓姆岙十七籮那爿地,田偏路遠,將稻谷從田里挑到馬路上,需走上一里多的田墈,再用手拉車拉回操場翻曬。要是一天割不完,天黑前,還得扛著打稻機這一重物,想想都費勁,非得請力氣大的村民幫忙不可。為了省些力氣,還要跟住在高爿地的那戶人家說好話,將打稻機寄存在他們家走廊上一個晚上。
7月30日下午,爸爸把弟弟也叫上了。為了給枯燥的割稻來點趣味,爸媽、弟弟和我四人之間互相比賽,還給弟弟劃出一小塊,說那是臺灣島,割完了,臺灣也就解放了,他就可以去玩了。就這樣,你追我趕,結果竟然提早完成了。
如果一切都能按事先計劃的進度割稻種田,在立秋前種完所有的田當然不成問題。但天天白天黑夜連軸轉,干了幾天,每個人都越來越疲累,越往后速度就越慢,尤其是像我這樣平時很少干體力活的人,早就渾身酸痛、眼冒金星了。要是天黑了還在水田里干活,蚊子就像轟炸機,圍著你嗡嗡嗡地叫個不停,咬得你渾身起包,又癢又惱。
那天下午,打完稻回家,夜色中我手拿鐮刀爬上山坡上的小路時,一不小心竟然踩到了一條蛇,左腳第二個腳趾頭被蛇咬了一口。我驚呼一聲“啊唷”,走在身后的父親急忙問:“沒事吧?沒事吧?”他手足無措,只是叫我快點趕回家,幸好我還能自己走路,腳趾頭好像也沒有馬上紅腫起來。回到家,隔壁的阿姆過來一看,說:“應該是無毒的水蛇咬的,不是毒蛇,要不腳早就腫得像饅頭了。”阿姆的小女兒比我大兩歲,前一年曬稻草時曾被毒蛇咬過,整只腳很快全腫起來如蓬松的饅頭,不能下地走路,后用土草藥敷了好幾個月才好。
小溪邊的俗話說:被水蛇咬的人會有好運氣。我就指望著哪天會有好運降臨。果不其然,第三天就有同學來通知我,我已如愿考上了自己喜歡的專業……
通常,頭天割完稻,將稻稈一把把捆好排在田墈上,第二天上午整理好水田,下午就開始插秧,天黑前,金燦燦的水稻轉眼間就變成了綠油油的秧苗。
家里缺人手,一畝多的稻田,從割稻到插完秧,通常需要三天時間。父親講究種田時的品相,高標準嚴要求。他認為,一丘田要有田的樣子才能插秧,比如:稻田的泥土必須全部翻新、松動、耙平,田壁整潔不留任何雜草,田墈削得清光漂亮。因而,頭天上午爸爸趕牛翻土耙平時,我就拿鐮刀清理雜草;中午,父親再抓緊時間削完田墈。吃完午飯,父親喜歡去家東邊關公廟的石板地上躺一會兒,石板地涼涼的,午休特愜意。下午三點左右,太陽開始西斜,田水不燙腳時開始種田——要不然,嫩綠的秧苗會被燙死。
做什么事都一絲不茍的父親,種田就更講究了,他要求插的四棵秧苗成正方眼,橫豎都是筆直的。一般人都認為只要豎行是直的,橫的彎來彎去都在田里彎,有什么關系呢,還不一樣割稻?但父親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標準。他還要求每棵秧苗之間的距離在三十公分左右,說這樣日照充足,稻谷才會飽滿,不爛腳。這或許是他種的水稻總是全村最好最大的關鍵原因。
就這樣,十多天中,全家人鼓足干勁,起早摸黑,總算基本忙完六丘田割稻種田的活兒。因人手太少,我們成了全村最后一戶種完田的,這在隨后的數十年中成了常態。好在父親精心管理的秧苗抽芽多、品質好,轉移到大田后,沒過幾天,就日長夜奓,很快就追上了那些人家早種幾天的水稻。收割晚稻時,那稻穗無疑又是全村最大的,人見人夸。
3.
小麥,也是小溪邊的主要農作物之一。秋末,那一爿爿溪灘地,重新翻整后,再一行行灑下小麥種子。一到冬天,溪灘上一整片全是綠油油的小麥。當時我家門前全是各家各戶的菜園子,沒建什么房屋,站在二樓廊下,可以遠眺溪灘地,一望無際的小麥地,靜靜地耐心地等著春歸。
在杭城讀書時,聽說城里人分不清小麥與韭菜,我甚感驚訝:它倆長得太不像了;但轉而想想,小麥剛長出、離地面才20厘米高時,遠看倒真有點像韭菜。只是在小溪邊,小麥會大面積種植,而韭菜一般只在墻角旮旯種上一點而已。至今仍讓我迷糊的一件事是:為什么越冬后的小麥,在開春前,有些人家會用腳踩小麥,說越踩分叉長出越多越稠密,收成越好。難道這是單子葉植物的特點?遠離稼穡,我沒有想著去細細考究一番。
小麥成熟是在每年的四月份,這時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家里缺糧食的,最難熬的日子就開始了,前后有半個月左右。記憶中,那段日子,媽媽時常會將牛欄間谷倉里的稻谷偷偷地送一些給姑姑,我們看到了也不會告訴爸爸,免得他心里不舒服。爸爸對姑姑是沒得說的,要是他偶爾與媽媽吵嘴了,媽媽生氣不做飯,他就會請姑姑來給我們做飯,但他認為姑姑家里缺糧,是姑姑的丈夫不勤快導致的。其實,那時缺糧食的人家比比皆是。過了這段日子,姑姑家種的番薯、川豆、冬瓜、豇豆什么的長成了,她總是挑最好的,送給媽媽。后來,姑姑的兩個兒子和女兒都成家立業,條件好起來不愁吃不愁穿,但姑媽的這一習慣多年未改。每次我回小溪邊,媽媽拿出紅薯、芋頭煮時,會順口說“這是姑姑送的”。
媽媽凡事追求完美,她總認為田芯村的師傅磨的小麥粉白一些。機器磨的小麥粉,一般分白粉和二子粉,白粉用來搟面皮、包扁食、做包子,而黑乎乎的二子粉只能做面條。為了多出點白粉,媽媽總讓哥哥挑著一擔一百來斤的小麥去田芯村磨粉。后來因為修建里石門水庫,田芯村的人絕大部分都移民走了,碾米機器間應該早就埋在水庫底了。一次聊起此事,媽媽還笑呵呵說:“那白粉做成的包子,手不干凈的人一按一個印。”
在小溪邊,小麥粉的主要用途是做手搟面和面皮。手搟面,可以用二遍粉黑一點的切。姐姐揉的手搟面總是不夠硬,常叫我幫忙,說我的手勁好;而面皮,必須用頭遍的白粉,最后要拉長,差的粉一拉就斷。水平高的磨粉師傅,頭遍磨出的白粉會更多一些,這也是媽媽每年要到離家三十多里的田芯村去磨過年粉的原因。
每年正月初二,隔壁鄰居三家人會聚在一起做過年的豇豆包子、洋糕等,三家的灶臺上都碼著一人多高的蒸籠。媽媽置辦了一整套品質上乘的蒸籠,蒸的時候,一點都不漏氣。蒸出的包子、洋糕,白白的,漂漂亮亮。而且,用糕水做成的包子會越蒸越白。那洋糕,媽媽會拿出一部分切成片,烘干,就成了過年時最受小孩們喜歡的零食。
(作者單位:最高檢檢察理論研究所)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共建亞歐大陸美好家園
- 這座有著2500多年歷史的中亞古城,曾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樞紐,連接起古代中國、波斯和古印度,見證了“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詳細]
- 法治日報 2022-09-18
加強國防教育 增強國防觀念
- 加強國防教育增強國防觀念各地扎實推進貫徹《關于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全民國防教育工作的意見》(2022-09-18)稿件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權威發布...[詳細]
- 新華每日電訊 2022-09-18

《人民日報》點贊山東陽谷新青年薛景霞:“科學化養殖”奏響美妙的田園交響曲
- 文中聚焦來自山東省陽谷縣的“全國鄉村振興青年先鋒”——薛景霞回農村創業、探索科學化養殖道路、帶動周邊群眾增收脫貧的故事,看他如何以...[詳細]
- 齊魯網 2022-09-18
“心本教育”推動學校持續優質發展
- 張兆偉先后榮獲“全國特色教育先進工作者”“全國家庭教育知識傳播激勵計劃卓越人物獎”“全國教育創新優秀教育工作者”“山東省十大杰出校...[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2-09-17
破解“唯分數論”的必然依歸
- ■教育這十年親歷者說作為一名長期扎根高三一線的高中校長,我認為構建多元評價選拔機制是高考制度改革創新的應然之舉,是多年來破解“唯分...[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2-09-17
發揮督導優勢 為“雙減”持續發力
- 一年來,教育督導戰線把“雙減”督導作為一號工程,對“雙減”政策落地起到了巨大督促、保障作用。教育督導應充分發揮制度優勢,為“雙減”...[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2-09-17
煙臺萊山區“三招”并舉 持續推動打擊整治養老詐騙宣傳工作走深走實
- 自全國打擊整治養老詐騙專項行動開展以來,煙臺市萊山區堅持多點發力、“三”招并舉,聚焦養老詐騙常見類型開展全方位、多層次宣傳,切實推...[詳細]
- 中國日報網 2022-09-17
為異域友人送去“Made in China”
- 一列列貨運班列有序駛出,宛若一條條馳騁八荒的長龍。2017年6月24日,滿載貨物的中歐(青島)貨運班列從位于青島膠州的中鐵集裝箱青島中心...[詳細]
- 人民政協報 2022-09-17
長安號:“絲路”古道上暢行的“鋼鐵駝隊”
- 十多年來,中歐班列運送貨物種類不斷擴大,運量持續增長,維護著國際產業鏈的穩定通暢,也成了沿線國家互利共贏的橋梁紐帶。當地時間9月9日...[詳細]
- 人民政協報 2022-09-17
漫步晴川閣,觸摸民族精神源頭
- 瞿祥濤禹稷行宮武漢大禹文化博物館供圖大江大河皆有源頭,民族精神亦是如此。武漢大禹治水傳說講述的是堯舜禹部落聯盟時代,長江、漢江流域...[詳細]
- 中國文化報 2022-09-17
城頭山:古老而年輕的家園
- 徐虹雨城頭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澧縣縣委宣傳部供圖9月,在縷縷稻香中,我走進湖南常德澧縣,走進位于澧陽平原的城頭山。護城河在東南面和正...[詳細]
- 中國文化報 2022-09-17
《資治通鑒》為何無可替代
- 《資治通鑒》是我國最大的編年體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學者司馬光主編,記載了從戰國到北宋成立之前1362年的歷史,涉及22個王朝,共300萬字...[詳細]
- 光明日報 2022-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