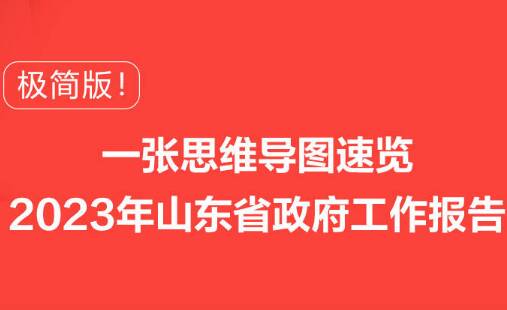如飛如翰,如江如漢
來源:光明日報
2023-01-15 13:49:01
原標題:如飛如翰,如江如漢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如飛如翰,如江如漢
來源:光明日報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筆談】
編者按
金文又稱青銅器銘文,是指鑄或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商周金文內容豐富,反映了商周王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生活等多方面的場景,是研究中國古文字、先秦語言與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資料。近年來,伴隨商周考古發掘工作的深入開展,許多重要的金文出土,極大地促進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本期《語言文字》即將金文與傳世文獻及考古材料相結合,探索西周時代的國家治理與文化奧秘,亦借以說明金文的珍貴學術價值。
在《詩·大雅·常武》中,“如飛如翰,如江如漢”被用來形容西周王朝軍隊征服南國之勇武。西周時周人所言之“南國”位于王朝領土“南土”之南,大致包括今江蘇、安徽境內之淮河流域,今河南境內淮水以南區域,南陽盆地以南與今湖北北部之漢淮平原。終西周一世,對“南國”區域的經營,一直是西周王朝最重要的政治、軍事與經濟行為,但傳世典籍中有關記載極為稀缺。我們依賴金文并結合考古資料才對這段歷史有了較為深入的了解。
周人早在克商以前即開始經營江漢流域。《毛詩·召南·甘棠》序中講到召公教化于南國的事跡。西周王朝建立之初,漸將漢東與淮水以北大部分區域控制為“南土”,并在邊域上設“侯”。“侯”是西周王朝外服軍事職官,有防衛疆域與開疆拓土的職能。大保玉戈銘文記載了王命令大保(即召公)去省視南國。召公循漢水東行代表王慰問南方的邦君諸侯,宣示王朝對“南土”的統治權。西周早期偏早的伯[圖1]鼎銘文曰:“惟公省徂南國,至于漢,厥至于?。”這里的“?”即河南漯河近淮水的胡,王朝在此封有?侯。由南土侯國的位置即可以看出,當時西周王朝“南土”的邊域所在,自西南向東北,較重要的有厲侯(湖北隨州厲山)、曾侯(隨州葉家山一帶)、噩侯(隨州羊子山一帶)、應侯(河南平頂山)、?侯(河南漯河)、蔡侯(河南上蔡)、滕侯(山東滕州)、薛侯(同上)。由以上侯國所在位置連起的南土邊域線至西周晚期亦基本上沒有較大幅度南伸,主要原因當是淮夷的興起對周人南下的鉗制。
2018年,隨州棗樹林第190號墓出土春秋中期偏早的曾公[圖2]镈銘文曰:“王客我于康宮。呼【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門,質應京社,屏于漢東,【南】方無疆,涉征淮夷,至于繁湯。”皇祖是曾公的先祖,是西周初輔佐文王、武王完成克商大業的南宮適之子或孫輩,“我”在銘文中泛指南宮氏家族。由此文可知,昭王曾命令南宮氏建邦國于南土,其位置要能護衛蔡國與應國,成為拱衛漢東之屏障,并打通前往南方廣闊疆土的通道,要能夠向東涉水(汝水)去征伐淮夷,一直抵達繁湯(今安徽臨泉)。要滿足上述條件的地理位置只能在淮水上游以北,桐柏山脈北端以東。西周王朝應是自此時起,始將南國之淮夷視為重點。并將控制繁陽作為征伐淮夷的一個戰略目標。傳世曾伯[圖3]簠為漢東曾國器,簠銘中曾伯詡其武功,言能驅除淮夷而安治繁陽,從而占有銅、錫運輸之道的“金道錫行”。曾公[圖2]镈銘文中所云昭王命南宮氏“涉征淮夷”也應是為了控制繁陽,打通王朝獲取銅錫的通道。
但繼續讀上舉曾公镈銘可知,昭王在命令南宮氏執行防御與征伐淮夷使命后不久,又給南宮氏下達了新的任務。镈銘記曰:“昭王南行,豫(預)命于曾,咸成我事,左右有周。賜之用鉞,用征南方。”“于曾”即“往曾”,“昭王南行”指昭王要南伐荊楚。昭王曾兩次征伐楚,首次在昭王十六年。昭王所以要在南征前,變更先前命南宮氏駐扎淮水上游以北以對抗淮夷的計劃,而命其到今湖北隨州的曾地,并命之為侯,顯然是與南征荊楚的計劃有關。但這一戰略的轉變,很可能是由于淮夷的興起使繁陽所連接的“金道錫行”受阻,昭王希望能改由隨棗走廊南下,另開辟一條通往長江流域礦產資源的道路。近年的考古調查與發掘證實,在長江流域中部今武漢以東與東南,分布有密集的與青銅冶煉有關的采礦與冶煉遺址。昭王為達到此目的而要伐楚,應該是楚人在此時已威脅到周人南下。
隨州葉家山墓地出土西周早期偏早的荊子鼎銘文記述荊子作為“多邦伯”的一員在舉行盛大祭典時,兩次受到王的賞賜。荊子可能是先后奉事成王、康王的熊繹,居荊山,自稱“荊子”。1980年陜西扶風出土的生史簋銘文記曰:“召伯令生史,使于楚,伯賜賓。”“伯賜賓”指召伯將楚君贈送使節之禮物賜給生史。由這些器銘可見,在成康之時楚人與周人曾和諧相處。但至昭王時,竟要南征楚人,這顯然是由于楚的勢力鉗制了周人南下。靜方鼎銘文記錄昭王在成周令靜曰:“俾汝司在曾、噩師。”這是昭王在十六年親征以前安排王朝卿士治理駐屯于今隨州曾、噩兩國的王朝軍隊。但昭王十九年二次南征時,涉漢水時出意外,《史記·周本紀》寫道:“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西周王朝打通隨棗走廊直接攫取長江中游資源的戰略設想亦因南征荊楚失利而放棄。不僅如此,周初在今漢東一帶的封國、布設的軍事駐屯地均發生變動。位于隨州葉家山的曾國墓地下限只到昭王時,西周中、晚期姬姓曾國的蹤跡迄今尚待探尋。
金文材料證實,自昭王時即已循淮水西上,阻斷“金道錫行”的淮夷,在穆王時更直接威脅到成周。穆王早期的錄卣、錄尊銘文記述:“王令曰: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圖4]”,現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館的[圖5]甗銘文曰:“師雍父戍在古[圖4],[圖5]從,師雍父[圖6]使[圖5]使于?侯。”師雍父派[圖5]到今漯河一帶出使?侯,顯然是為了聯防淮夷的事,由此亦可見,淮夷確是沿著淮水溯流而上逼近成周。1975年陜西扶風莊白出土的[圖7]方鼎銘文記王令[圖7]“率虎臣御淮戎”。“淮戎”即淮夷。同出[圖7]簋銘文記[圖7]率有司、師氏“搏戎?”,即搏殺淮夷至上文所言在漯河之?。
從金文資料看,自西周中期偏晚至晚期,西周王朝與淮夷一直處于博弈狀態。淮夷是一個包括若干族群(族邦)的大族團,同一時段有服從王朝統治的族群,也會有與王朝處于戰爭狀態的族群。西周晚期厲王之時,西周王朝與淮夷的矛盾進一步爆發。周厲王自制的?鐘銘文曰:“南國服孳敢陷處我土。”“服孳”是對淮夷的一種鄙稱,淮夷攻陷王國內地,于是厲王發動了王朝對淮夷力度最大的一次征伐,有相當多的西周晚期有銘器記載了這一場戰役。這場戰役的重要戰果是攻入了淮夷中心活動區域,即今江蘇境內,淮水與泗水交匯之洪澤湖地區。上引周厲王?鐘還記載曰:“王敦伐其至,撲伐厥都,服孳乃遣間來逆卲王,南夷、東夷俱見二十又六邦。”“遣間”即派中間人說和,可見淮夷雖遭受重創,但并未潰敗。噩侯馭方鼎銘文記厲王在此次攻伐淮夷回師途中路經邳地(今江蘇睢寧北),噩侯馭方在此慰問王,與王共行射禮與宴飲。西周早期時噩在隨州,至此時噩侯能在今蘇北之邳地會王,則其必是在昭王南征失利,漢東政治格局變化背景下有東遷之舉。但噩侯馭方恭順西周王朝的時日并不長久。禹鼎銘文記述噩侯馭方又“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歴內”,鼎銘竟驚呼:“嗚呼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國。”禹則奉武公之命以武公戎車與徒馭再次配合王朝西六師、殷八師伐馭方,親擒噩侯馭方。此役雖告捷,但西周王朝的軍事實力經長年與淮夷兵戎相見,特別是厲王對淮夷大規模用兵的過程中被嚴重消耗,加速西周王朝走向末世窮途。
禹鼎銘記厲王令禹伐噩侯馭方要“勿遺壽幼”,但2012年在河南南陽東北的夏餉鋪發現有春秋早期的噩國墓地,亦為前所未知。在第19號墓出土壺銘文言“噩侯作孟姬媵壺”,是噩侯為姬姓女子作陪嫁的銅器。這自然就出現兩種可能,一是姞姓噩侯已滅,此時的噩侯已是姬姓,仍沿襲“噩侯”之稱,屬于改封;二是姞姓噩侯家族仍在,只是遷至南陽,此乃為陪嫁自己女兒出嫁的姬姓女做器。相對而言,前者可能性大,當然何者為是,有待新的發現。
《詩·大雅·崧高》詠周宣王封申伯于謝(今河南南陽東南),“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即要申伯施其法度統理南國諸邦,并希望申國能成為拱衛南土之屏藩。此申國,在西周時亦稱“南申”,近年來多有“南申”銅器出土。1974年陜西武功出土的駒父盨蓋銘,記駒父慰問“南諸侯”,并且向南淮夷征取其“服”(布帛,或還有人力),可見西周末年,武力征服與強迫貢納仍是王朝對淮夷的國策。但終西周之世,王朝亦未能在淮夷區域建立治所。上引曾伯[圖3]簠銘文仍言其曾戰勝淮夷而控制繁陽,以打通“金道錫行”的功績。此足可見,直至春秋淮夷仍與周王朝爭奪對金道錫行與對繁陽的控制。
從西周金文、考古發現及典籍所見,西周王朝對南國的經營重心始終緊扣著對多種資源的攫取,亦與南國族群長期處于對立狀態,這也成為消耗王朝精力加速其覆滅的重要因素。由對金文與考古資料的研究,方使這段重要的西周歷史真相逐漸顯現。
(作者:朱鳳瀚,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考古發掘與金文考釋探索“曾隨之謎”
- 提到曾國,最著名的發現就是氣勢恢宏的曾侯乙編鐘,全套65件,總重超過2.5噸。近代以來,相當數量的曾國青銅器被發現,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詳細]
- 光明日報 2023-01-15
2023年“文化進萬家——視頻直播家鄉年”活動啟動
- 14日(農歷臘月廿三),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中央網信辦網絡傳播局在山東濰坊舉辦2023年“文化進萬家——視頻直播家鄉年”活動啟...[詳細]
- 光明日報 2023-01-15
山東省曹縣公安局舉行儀式將涉案財物集中返還給受害群眾
- 1月12日,山東省曹縣公安局舉行儀式,將被盜的汽車、手機、煙酒、現金等價值175萬余元的涉案財物集中返還給受害群眾。董西德攝[詳細]
- 人民公安報 2023-01-15
省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大會發言摘登
- 1月14日下午,省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在山東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15位委員圍繞科技創新、新舊動能轉換、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鄉村振興、...[詳細]
- 中國日報網 2023-01-15

新春走基層|巡防駐守除隱患 渤海長存“火焰藍”
- 煙臺長島海洋生態文明綜合試驗區消防救援大隊。長島大隊供圖在位于渤海深處、黃渤海分界線上的長島,也有同樣的一個群體,他們來自五湖四海...[詳細]
- 人民網山東頻道 2023-01-15
青島上合廣場項目建設按下“加速鍵”
- 近日,青島上合廣場項目順利完成首塊筏板混凝土澆筑工作,標志著主體結構全面施工拉開序幕,項目建設按下“加速鍵”。為確保首塊底板順利澆...[詳細]
- 中國日報網 2023-01-14
外國友人體驗“泰山花饃”
- 1月13日,數位外國友人應邀來到農家女花饃基地體驗傳統非遺面點文化泰山花饃。花朵、小兔子、葫蘆,還有配著綠葉的壽桃、福袋……在面點師...[詳細]
- 中國日報網 2023-01-14
濟寧微山:京杭大運河畔民俗薈萃年味濃
- 新春將至,濟寧微山縣夏鎮街道古運河旁,畫舫船游運河新年路線吸引不少游客來打卡。當地對接融入大運河文化經濟帶建設,實施國家大運河公園...[詳細]
- 中國日報網 2023-01-13
報告解讀丨矢志推進強省建設,五年來山東取得“三大標志性成果”
- 責編 徐皓[詳細]
- 光明網山東頻道 2023-01-13
扣好年輕干部廉潔從政“扣子”
- 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公報將“全面加強黨的紀律建設”列入今年重點工作,并強調“高度重視年輕領導干部紀律教育”。年輕干部事關黨和人民...[詳細]
- 中國紀檢監察報 2023-01-13
讓聽障人群第一時間得到警示信息
- 本報訊“過去,防空警報、地質災害等發布警示消息時,大多采用音頻方式。同時,報警、聲控燈光等以音頻方式發布的報警平臺和環境警示消息,...[詳細]
- 人民政協報 2023-01-13
推進山東半島城市群多層次軌道交通融合發展
- 山東省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期間,住青山東省政協委員張君聚焦“推進山東半島城市群多層次軌道交通融合發展”,建議健全省級城市群、都市圈多...[詳細]
- 人民政協報 2023-01-13